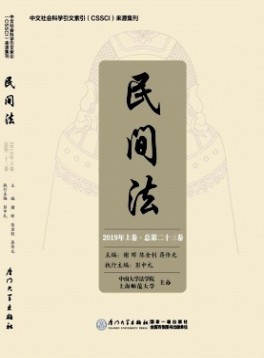民间音乐文化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3-03-23 15:24:07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民间音乐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作者:王文静 单位:河南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从文化学视角来看,开发本土的民间音乐资源是河南经济、文化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必然要求,是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一种“文化自觉”[2]。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自我认同,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且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去认识、看待自己的文化;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自我评价,不能局限于一地,既不能孤芳自赏,妄自尊大,又要从全国乃至全球的范围和发展的趋向,来考量自己文化的未来价值和导向意义。在地方高校艺术教育中融入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有助于大学生正确看待本土的民间艺术形式与文化,在进一步了解、认识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同时,逐渐加快本土音乐文化的自觉进程,对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有力推动作用。社会学价值从原始社会到现代,艺术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每个时期都有代表其最高成就的艺术类型,这些艺术无一不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民间音乐的产生、发展、变异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音乐的变异和更新,其自身不同程度地存留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积淀。因为有着深深的社会烙印,人们才能够在民间音乐的欣赏和表演中寻觅到过去历史时代的文化风采,才能够从民间音乐的音调中感悟到浓浓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气息。民间音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民歌,它是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也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的缩影。例如革命战争年代,商城县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因此而生的民歌多达百余首,如《打商城》《送郎当》《来了晴了天》《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一直传唱至今。作为集音乐、舞蹈、戏剧为一体的、我国独特的综合艺术形式———戏曲,同样也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精神。如建国初期反映广大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剧作,不仅出现了《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焦裕禄》等优秀剧作,更出现了建国以后戏剧创作的经典之作———《朝阳沟》。
《朝阳沟》是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接受思想改造的现代戏。就思想主题来说,《朝阳沟》正应和了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需求,体现了极强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在高校艺术教育中加入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既丰富了大学生的民间音乐知识,更有助于大学生更为直观地去感受、认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的精神实质,从根本上把握时代特征。教育学价值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影响下,人们的观念必然会产生一些混乱和迷茫,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对整个社会精神品质的构造无疑是最为直接和最具影响力的。因此,如何使我们的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社会理想,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蚀,崇尚精神之美,不断提高自身的辨别力和免疫力是当前教育战线上的重要课题。从民间音乐反映的内容来看,民间音乐直接反映人民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直接表达人民的心声、感情和愿望,成为人民表情达意最直接、最有效的艺术形式,人民的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从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在一首首的民歌、经典戏曲唱段中,无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反映了人民群众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高校艺术教育课程中加入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使学生在自觉欣赏与参与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诉诸和唤起人的情感过程中以审美的方式来培养和完善人的道德人格,以春雨般“润物细无声”来浸润每一位学生的心理情感等各个领域,进而促进人的心身健康全面发展。因此,民间音乐以其独特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途径渗透至学生的生活学习领域,具有独特的教育学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在传播学中,“自我传播指的是人自身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如感知以及感性到理性的意识和思维活动,如自吟、自唱等活动”[3]。在这一过程当中,大学生用整个身心来传达音乐信息,又用整个身心来接受传达来的音乐信息,他既是音乐的传播者,又是音乐信息的受传者。一切传播过程,都是在大学生自我欣赏音乐、自我弹奏、自唱自吟中完成的。通过这些活动,大学生可以得到内心的愉悦与精神上的满足。民间音乐积累了丰富的优秀曲目,它们按照人民的审美观在流传中千锤百炼、凝聚成富有高度艺术感染力的音乐形象,有的催人泪下、令人断肠,有的令人心旷神怡、兴奋愉悦,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和欣赏价值,是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更有一些稀有剧种,从唱腔、板式到乐器伴奏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使得大学生在对地方民间音乐文化有较为系统认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多方面的艺术审美能力。
在民族音乐教育的主旋律下将爱省、爱国主义精神传达给每一位大学生。通过作品的主题思想,加深大学生对本省历史,对社会进步的理性认识,从而产生一种精神,表现出大学生对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价值认同,促进形成一个渗透着“和谐”内涵的具有完美人格的高素质“真人”,进而达到高校校园真正的、理想中的和谐。匈牙利著名教育家柯达伊说过:“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自己的民族民间音乐,不把本民族音乐文化建立在自己的民间音乐基础之上,就会象飘莲断梗一样地在世界文化中漂泊,或不可挽救地消失在国际的半文化之中。”在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树立音乐教育多元文化观念,重视民间音乐文化教育,抓住民族音乐文化之根,是高校培养新世纪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根本保障。
篇2
1 多元化理论下民族钢琴音乐体系构建策略
1.1 制定科学完善的教学目标
民族钢琴音乐要想实现多元化发展,就需要不断吸收我国多样性的民族音乐,从而增强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发展水平。但是在以往的钢琴音乐教学中,由于教师对教学目标不够重视,导致教学方向和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影响到民族钢琴音乐的进步。当前我国许多高校在进行民族钢琴音乐教学时,虽然都涉猎到中国民族音乐,但是与本土民族音乐的介绍相对较少,这样使得学生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感受不到钢琴音乐与民族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降低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教师应该要明确自身的教学目标,找到更适合本学校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案,增强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的认识,在今后的学习和创作中能够将更多的民族音乐融入其中。教师在教学时,还要积极构建完善的钢琴课程体系,真正实现钢琴民族化教学,在教材的选用、教学曲目的确定以及演奏技能上更要突出民族钢琴音乐的特色。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努力为学生打造良好的民族钢琴音乐学习环境。
1.2 提升教师的民族音乐文化意识
教师在进行民族钢琴音乐教学时,应该要提升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意识,这样才能够达到教学目标,为学生今后民族钢琴音乐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在传统的钢琴教学中,教师大部分比较重视外国经典钢琴作品的讲解,从而忽视了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教学,学生长期在这样的状态下学习,无法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也就不能够将钢琴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的融合,从而降低我国钢琴民族音乐的发展质量。提升教师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质量,首先,就要增强教师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认识,重视民族音乐的多元化,了解各个民族音乐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给学生介绍更多的音乐知识,满足他们民族钢琴音乐的学习需求。其次,要努力实现音乐教师教学思想的多元化。钢琴音乐教师在教学时不仅需要有比较高的专业技巧,同时还要有着比较高的音乐文化素养,在思想上能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吸收百家文化之长,汲取我国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为学生创建更加宽松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调动他们学习民族音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今后的创作中将钢琴与民族音乐完美融合,促进我国钢琴民族音乐更好的走向世界。最后,教师要实现授课形式的多元化。钢琴技巧的提升不仅需要学生的日常练习,同时也需要教师的良好指导。教师可以采用欣赏式、讲座式以及比赛式的教学形式来讲解钢琴音乐知识,调动他们学习民族钢琴音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3 拓展多元化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
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的民族音乐文化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这样就导致大量民族音乐资源文化的浪费,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高校作为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基地,教师应该要不断丰富其多元化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给予学生更多的民族钢琴音乐学习指导,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钢琴音乐学习的重要性,从而为我国今后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拓展多元化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教师就要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来制定教学方案,让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有更多的学习兴趣,感受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魅力。教师也要积极推动相关理论知识的构建,如要加大对一些民族音乐的调研研究,分析出这些民族音乐的特色,并结合这些特色来探讨相应的发展理论,找到更多的民族音乐发展空间,为我国钢琴民族音乐的进步提供强大的理论保障。在教学理论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情感培养,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在学习时可以将民族情感融入其中,这样既能够提升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的理性认识,又可以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满足他们的钢琴音乐学习需求。
1.4 构建完善的民族钢琴音乐实践环节
篇3
撒拉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一带。撒拉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两类,其中民间音乐较为丰富,尤其是以民歌为主体。撒拉民歌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乐器品种较少,普遍流传的仅口弦一种,未有独立器乐曲。纵观几十年来学者们对撒拉族音乐所做的工作,主要成就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撒拉族主要聚居区的民歌进行了重要的调查和记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曲谱资料,为撒拉族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60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所拟定了有关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草案)》,根据这一精神,青海和甘肃音协组织了音乐家深入撒拉族地区采风。据资料记载,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杜亚雄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前往撒拉族地区采风,发表了一些介绍、研究撒拉族民间音乐的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河畔红花――介绍撒拉族民间音乐》①。
1979年《中国民歌集成》编纂工作得到恢复后,各省对各民族民歌进行了普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收集撒拉族民歌32首。1994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收录了杨鸣键的《撒拉族民歌简介》一文,对撒拉族民歌做了全面介绍,也对撒拉族民歌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共收入撒拉族民歌70首,2000年再次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收入撒拉族民歌71首。除此之外还有《青海花儿曲选》(青海群众艺术馆编印,1979年)其中收录撒拉族花儿41首;《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60年编印),其中收集撒拉族花儿11首,宴席曲4首、号子6首、其他4首。《中国曲艺集成》(青海卷)回族撒拉族部分中收录打搅儿曲目1首;《驼泉清清――歌唱循化歌曲选》,由青海本地作曲家及音乐爱好者创作撒拉族歌曲共188首;《青海撒拉族花儿曲选》马正元编,名人出版社,2004年;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青海民间小调》,1978年。关于舞蹈的有《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青海卷),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由中国戏剧家学会青海分会、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其中收录了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青海民族民间舞蹈集成》1989年,介绍了撒拉族舞蹈概况,收录了民族舞蹈7部,并在其中附有舞蹈图示和乐谱。
二、音乐文化著作中对撒拉族传统音乐的介绍
从中国少数民族大的民族领域研究音乐文化的著作,其中有的篇章涉及了撒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撒拉族音乐及其风格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介绍,使撒拉族民间音乐得到不同程度的昭示
综合类主要有: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本书中按艺术体裁将撒拉族民歌进行了分类;袁炳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撒拉族的音乐史分为四个部分;乔建中的《中国经典民歌鉴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杜亚雄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蔡廷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54页,1989年)编写了《撒拉族音乐》部分。此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对“撒拉尔玉尔”“撒拉号子”“撒拉婚俗”“撒拉曲”“撒拉少年”“撒拉戏”条目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对“撒赫稀亚格拉”(哭嫁歌)、“撒拉尔玉尔”“撒拉花儿”等条目均有介绍。
三、对撒拉族音乐及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主要论文:钟子林《撒拉族音乐概况》,中央音乐学院院刊,1959年总89期;张谷密.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3);马忠国.撒拉族民歌概述[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04);范晓峰.撒拉族民歌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01);马盛德,司马力.试谈撒拉族舞蹈[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03);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式旋律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8(04);张静轩.撒拉族民歌及其音乐特征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02);王海龙.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07);张云平.撒拉族哭嫁歌艺术特征研究[J].民族艺术,2009(02);晁元清.撒拉族民歌《阿里玛》遐想[J].音乐创作,2010(03);王玫.浅论青海撒拉族民歌的多元文化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韩建业.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J].青海民族研究,2005(01);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宴席曲研究[J].民族艺术,2009(03);郭德慧.撒拉族民间音乐文化构成因素初识[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2);郭晓莹.土族花儿和撒拉族花儿的艺术共性[J].中国土族,2008年夏季号。
除此之外,涉及到音乐艺术方面的论文还有朱刚、李延凯的《撒拉族民间文学简介》,马学义的《撒拉族民进文学简介》,马成俊的《撒拉尔歌谣初探》。
(二)论文集:《百年撒拉族文集》其中收集了21世纪以前撒拉族论文,其中包括了音乐类的有张谷密的《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马忠国的《撒拉族民歌概述》,马盛德、司马力的《试谈撒拉族舞蹈》等。
(三)专著:苍海平的《撒拉族音乐文化概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9月。本书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撒拉族民族民间音乐,参考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分类方法,对撒拉族现收集到的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收集到的100多首民歌逐一进行了极细致的曲式分析和研究。
在音乐创作方面。创作歌曲《新循化》《阿里玛》等;歌舞音乐《摘花椒》《黄河放排》《驼泉清清》《打墙》等。舞蹈方面有1989年由蔡廷玉、尹崇尧编剧的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
近年来,撒拉族的新型歌剧也有了新的发展。比较优秀的剧目有撒拉族花儿剧《驼泉清》《打麦场上》等。随着时代的前进,撒拉族音乐将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它将继续不断地激励撒拉族人民在增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教育和娱乐作用。
结语
撒拉族音乐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现发表的论文只是简单地将现收集到的撒拉族民歌做了分类和说明,并没有新的挖掘和整理。2.研究的视野还不够扩展,至今也没有涉及到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的著作和论文。3.关于撒拉族音乐的渊源没有论文进行分析和研究。4.撒拉族民间音乐仍需深层次挖掘和整理。5.对撒拉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加强力度。6.撒拉族音乐研究还处于以个人研究为主、各自为政的状态,现在的研究成果零星散乱,且深度不够。
篇4
一、研究现状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著《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著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1.对于白族传统音乐本体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谓音乐本体,即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和声、曲式等。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较多的研究满足于对白族传统音乐中某类音乐或某地区的音乐作泛泛的介绍或基础性的资料梳理工作,没有典型曲例,更没有音乐分析。如果我们对于一些正在面临消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始终深入不到音乐本身,不研究音乐,只介绍大概情况,只满足于音乐形态的最表层描述,那么对于该种音乐文化被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史料发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交叉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其历史发展问题关注得非常少,或者说,有关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多数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时间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民族音乐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特点,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会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3.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的“体验性”和“叙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满足于把“田野”仅仅当作资料收集的场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对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调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体验性”和“叙事性”的表述。这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或称观念,在目前的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显然还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目前的发展现状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传统音乐和其他的民族音乐一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从音乐思维方式、传承方式、表达方式和音乐制度、活动场合、传播要求等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那么,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甚至还可以由此引申出,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及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白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种种,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三、结语
结合白族音乐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回顾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乐的探索期,八十年代为白族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乐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则是白族音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特征也是与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我们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云南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抢救及理论建设、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坚实的工作基础。同时,当我们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兴高采烈时,也应关注到这样的现状:不少珍贵的音乐遗产正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一些老艺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们对民族音乐包括白族音乐的考察、采集、整理、保护等工作远未结束。笔者深信,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工作会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一样,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注释:
①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j].人民音乐,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③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赵全胜.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j].音乐探索,2006,3.
⑤冯洋.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4卷.
⑥关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
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段寿桃.白族打歌及其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张文,陈瑞鸿主编.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赵宽仁.白族的音乐[j].人民音乐,1961,11.
李晴海.西山白族风情与“西山白族调”[j].音乐初探,1985,2.
饶峻妮,饶峻姝.略论大理白族情歌中的白由超越性[j].大理学院学报,2009,5.
赵怀仁.论白族民歌曲调的忧伤色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杨秀.大理白族原生态民歌的音乐特性[j].民族音乐,2008,3.
⑦大理市文联等编.白族大本曲音乐[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⑧董秀团.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j].思想战线,2004,4.
⑨此类成果还包括有:杨亮才.谈白族大本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伊铨.论大本曲之“三腔”白族传统曲艺大本曲的三腔介绍[j].民族音乐,1987.
李晴海.白族民间大本曲概述[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6,4.
丁慧.云南白族大本曲的音乐特征[j].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09,1.
杨红斌.大理白族民间音乐的类型及表现形式[j].民族音乐,2008,3.
⑩张涛.省级在研课题.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
{11}张绍奎.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j].民族音乐,1987,2.
{12}寇邦平.白族吹吹腔初探[j].民族艺术研究,1988,5.
{13}李晴海.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1989,5.
{14}傅媛蕾.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15}其他还有:蒋菁.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2.
尹铨.白剧音乐发展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1988,3.
杨晓凡,马永康主编.白剧风采[m].内部资料,2006.
丁慧.云南白剧“吹吹腔”夕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1.
{16}李洋.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j].民族艺术研究,2000,3.
{17}赵全胜.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j].大理学院学报,2009,1.
{18}杨红斌.白族八角鼓的演变[j].民族音乐,2008,3.
{19}此类研究还包括:杨育民.大理、洱源地区白族民间唢呐乐曲调式初探.民族音乐,1984,5.
马建强.云龙白族唢呐及其音乐形态探析[j].民族艺术研究,2001,6.
黄锦华.白族唢呐锣鼓乐浅探[j].民族艺术研究,1999,4.
徐傲丹,吴永贵.白族吹打乐探究[j].民族音乐,2008,4.
{20}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21}潘晓敏,山雨彤.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2.
{22}孙淼.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j].中华文化画报.
{23}此类成果还包括有: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羊雪芳.剑川白族民间舞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j].民族艺术研究,1999,5.
聂乾先.关于白族舞蹈——从大型白族歌舞《玉洱银苍》说开去[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聂乾先.“白族打歌《考略》与《质疑》”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24}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5}何显耀.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6}羊雪芳.剑川洞经音乐调查[j].云岭歌声,2003,4.
{27}张文.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j].音乐探索,2003,1.
{28}还有:罗明辉.关于洞经音乐问题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29}杨明高.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j].艺术探索,1997,s1.
{30}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j].音乐艺术,2005,1.
{31}此类成果还有:石裕祖.大理地区白族佛教乐舞纵横考[m].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云南民族舞蹈论集.1990.
张逾.白族阿吒力佛教乐舞[j]民族艺术,1998,1.
石裕祖.白族巫舞及其流变[j].民族艺术研究,1998,3.
{32}杨曦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9,2.
参考文献:
[1]吴学源编著.滇音荟谈——云南民族音乐[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2]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晴海.“白族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篇5
一、有关阴山音乐文化的诠释
这是本次学术会议的重点研讨议题之一。这方面的论文集中就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等问题做了必要和细致的探究,采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和视野,以有利于阴山音乐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本次会议把阴山音乐文化与乡土音乐教育研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讨很有意义,很有战略眼光。这是两个既可相互独立,又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课题。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渠道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民间活态的自然传承;另一个即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传承。我谓之“双渠道传承”,后者正是我国百年学校音乐教育中所严重缺失的。只有让青少年们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使民族文化之根深深扎入大地,继而枝繁叶茂”。
赵宋光(星海音乐学院)在题为《阴山南北河套内外,地理迁活历史》的论文中,通过从古到今这一地域的35项可以载入史册的事项的详尽描述中指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几十个古代民族曾在这里交汇融合。几大文化板块交接在近代史上撞击出绚丽的火花,当代航天飞船返回地球恰恰选中这里的一片平坦的草原为适宜的着陆场等,这一切历史事项又将预示着什么样的经济、文化前景呢?解答这一历史之谜是当代文化研究的职责”。
冯光钰(辅仁音乐学院)在《阴山地域文化区传统音乐的保护与当代生存发展之路》的论文中指出:“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中部及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是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有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品种,应当从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三方面揭示这一地域文化区传统音乐的特性;进而去寻求这些传统音乐当代的生存之路。”同时他还提到:“值得高兴的是,继长江、草原的纵横交错板块状地域音乐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现今又由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阴山音乐文化与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研究’学术研讨会,开启了‘阴山山脉音乐文化’研究的进程。这次学术研讨会将‘阴山音乐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无疑是很有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良好开端”。
潘照东(内蒙古社科院)在《阴山文化及其历史影响》的主题报告中指出:阴山音乐文化是阴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探索阴山音乐文化,就有必要对阴山文化做全面的诠释,从阴山的定位、内容、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做出翔实、严谨的学术阐释。并引用明代顾炎武之言,以“得阴山河套得天下、阴山河套安天下安”之言,强调了阴山独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阐述了阴山文化是联系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纽带,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阐述了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多元复合型文化的特点,内涵、底蕴更为丰富,历史影响更为深远广泛。
柯沁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高举阴山文化旗帜,探寻啸乐文化源流》的论文中首先高度地评价了包师音乐学院高举“阴山音乐文化”旗帜的深远意义。并通过“阴山文化”与“泛阴山文化”区域范围的阐释中指出,必须承认阴山文化圈的文化是以草原原生文化为基本形态,是最为生动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中实现文化变异和创新发展起来的次生文化、共生文化。三种文化共同组合为中国北方富有特色的复合文化。并对“啸乐文化”的界定、内涵与外延,“啸乐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炜民(包头师范学院历史学院)对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阴山文化研究》课题做了介绍,并就此课题选题的意义和思路,中国文化和阴山文化的关系;阴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他强调阴山文化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没有真正反映出来,并呼吁深入地挖掘阴山文化是我们的职责。
张贵(包头医学院历史学院)在发言中认为,阴山音乐是中华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阴山音乐有着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魅力,发掘阴山音乐文化资源,创作阴山音乐精品,必将推动本土音乐的发展,促进我国音乐的繁荣。
二、蒙汉交融的区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
研讨会将乌拉特、鄂尔多斯音乐文化、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方面的研究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体现了本次会议对蒙汉交融的区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特别关注,并试图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这些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明确这些姊妹艺术在其整体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
郑少如(西口文化研究会)在《再论西口文化》的论文中指出:“西口文化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流汇萃之地,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汇交融之果,因此有着鲜明的特色,是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是草原文化最为闪光的一颗明珠。”并通过西口文化与草原文化;西口文化与包头的品牌文化;西口文化与晋商文化;西口文化与旅游文化四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包头是个非常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又是晋商发展延续的脉络,所以包头要打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以使相关产业才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柳陆(包头文联)在题为《西口路上的苦歌与心歌》的论文中通过多次对西口路的田野调查认为:“走西口的人共同唱的这些民歌,是在黄土高原那些穷乡僻壤缘起的,其传承流变中经受苦难历程。大量的民歌所反映的生活、表现的主题、演唱的风格、抒发的情感、律动的节奏,无不带有比一般民歌更加浓厚的悲切色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民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哭”出来的。山曲儿作为民间乡土文学,它最大的特点是方言的使用。也正是这些大量的有生气的方言,才丰富了这些山曲儿的艺术魅力,使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李野(内蒙古诗词学会)在其论文《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漫翰调与二人台》中认为:“包头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包括北方许多游牧民族和汉族)的活动区,因此,包头的历史,是历代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编写的。包头的文化,也是先后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包头的文化,是一种多元融汇的文化。所谓多元融汇:一是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二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融汇;三是多种地域文化的融汇。”由于蒙汉两族音乐长期的密切接触和双向交流,所以二人台的唱腔和牌曲,从旋律、节奏、发音吐字的方法到器乐的演奏技法,无不渗入了蒙古族音乐的一些影响、一些韵味。而融入二人台音乐的蒙古族乐曲,也受到汉族民间音乐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同二人台音乐浑然一体。漫瀚调的曲调主要来自鄂尔多斯高原的蒙古族短调,虽然也有一部分源于汉族的山曲儿,但从总体来讲,漫瀚调是蒙古族民间音乐同汉族的民间诗歌的融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风搅雪”,鲜明地显示出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广度与深度。
王星铭(包头市广电局)以1978年包头日报曾开辟了一个专栏“以李野老师为旗帜号召二人台必须走戏曲道路”为话题,谈起了当时自己对二人台体裁的困惑,并多年进行田野采风,曾在二人台研讨会议上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二人台有曲目和剧目组成,二人台艺术形式应包括二人台坐腔、二人台舞蹈,二人台歌曲、二人台戏曲等多元形式,二人台打坐腔中存在着多元发展的可能,二人台只是一个戏路的形式还不是戏曲的形式。”同时谈了对漫翰剧和包头的音乐风格的认识。
苗幼卿(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在《二人台牌子曲探究》一文中认为,二人台牌子曲系内蒙古西部区最具影响的民间丝竹乐种,要早于二人台的形成,曲牌源于多方面,既有古乐曲遗存,也有从蒙古族民歌和汉族民间音乐中衍变而来。同时,还吸收了部分宗教音乐,系中原汉族移民音乐文化与当地蒙古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艺术结晶。
李红梅(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关于二人台传承与发展的的几点思考》的论文中提出;“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变革,二人台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日益严峻和复杂,面对新生代对二人台喜爱程度的弱化趋势,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发展二人台音乐,使二人台的音乐精髓得以保存,艺术生命得以延续,是摆在音乐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二人台的继承与发展中需要通过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的统一,程式性与即兴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方面来继承、发展二人台”。
臧志君(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在题为《从蒙古民歌的多样性看西部民歌的多样性》的发言中讲到:“在研究蒙古族民歌时看到西部民歌也存在多样性的特点,近年来发行了民歌典藏———三代长调歌唱家的原声汇萃、六大民歌色彩区民歌经典,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于不同色彩区受所居住的如山地、河流等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所以其曲调、风格、形态各有不同”。
杜容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发言中深入浅出地讲解并演唱了不同的漫翰调、爬山调、山曲儿、风搅雪,从而直观形象地介绍了各种姊妹艺术之间风格的不同。她强调指出:民歌是人类文化最珍贵的部分,因为民歌是从泥土中来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研究民歌要深入下去,由对文化的认识引申到对民歌的进一步认识。她特别强调漫翰调的传承靠年轻人,靠学校。希望能办一个传承班。
刘新和(内蒙古艺术编辑部)在其论文《爬山调美学四题》中认为:“言爬山调美学,必须先言爬山调;言爬山调,必先言‘西口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如果没有西口人,便没有爬山调;西口人是一个由来自内地移民与其后代构成的复合体。近年来,学界将由西口人创造的文化称之为‘西口文化’。透视爬山调,人们不难看出西口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美学价值。爬山调全面、系统、直接地反映了明中期以后延至清、民国及以后西口外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描绘的是具有多种多样画面的场景,表现出不同层面人物心理与思想状态,质朴、深邃、凝炼,特别是对爱、爱情的理解与表述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马春生(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爬山调文化艺术研究之思考》的论文中指出:目前对爬山调文化艺术科学的认识与梳理还缺少大文化的观念与多元文化、异质文化共生的理性分析,缺少从爬山调产生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爬山调生成的环境,爬山调曲式结构、音阶、音调、节奏、节拍等的运用,爬山调歌唱形式及歌唱方法,爬山调歌词的艺术特色研究等方面的系统梳理与阐述”。
姜晓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试论爬山调与信天游之比较》一文认为,爬山调和信天游基本上同属于一种类型的民歌体裁,因此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采用两句一组,每句字数不限,多用比兴的手法,并在歌词中出现大量的方言土语,使其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同时,由于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不同,两者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朱文成(内蒙古河套大学)在《音乐艺术的常青树———山曲儿的艺术特点及审美》的论文中指出:“山曲儿短小精美,琅琅上口,是深受晋、蒙、陕、冀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应当呼吁共同抢救、挖掘、整理创新民族音乐,使山曲儿扎根于民族历史与生活的土壤中绽放异彩”。
胡佳(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论文《浅析内蒙古西部汉族民歌的艺术特征》中通过对于爬山调、漫翰调的历史来源及艺术形式、题材内容进行分析,概括出各自具有多元化和独特化的艺术手法和特点。
贺宇(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探寻格亥图村秧歌艺术的载体———秧歌队》的田野调查报告中指出,格亥图村的生活环境和秧歌队产生的土壤血脉相连,要想了解跑圈子秧歌在格亥图村的重要位置,首先要了解该村秧歌队的构成。秧歌队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时代的产物,从队员的地位以及队员身份的演变中可看出时代的烙印。一个地区民间音乐的形式,常常是折射这个地区音乐生活的一面镜子。对于当地秧歌队员的生活、生平以及周围村民对他们表演的评价、观察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寻找传统文化历时与共时的轨迹,有利于深化对跑圈子秧歌的理解、认识和研究。
三、环阴山地区宗教仪式音乐及音乐文化志的考察与研究
这是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学术研究方向是通过对宗教音乐在宗教和宗教仪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宗教音乐传播的本土化、变异等问题深入调查,仔细分析,拓展其研究领域后展开的,并通过图、谱、志等音乐文物的出版介绍,为研究阴山音乐文化提供更为翔实丰富的实证。
杨玉成(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其论文《18世纪蒙古族音乐巨擘梅日更葛根》中讲到:18世纪上半叶,蒙古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梅日更葛根。他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且一生孜孜不倦,硕果累累,在佛学、经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医学等诸多领域中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特别是为藏传佛教的蒙古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音乐巨匠,从18世纪中叶以来,内蒙古西部乌拉特各旗大大小小二十几座寺院,一直用他编创的曲调念诵他翻译编配的蒙文经文。他一生作有大量的歌曲作品,这些歌曲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歌体裁,乌拉特人称之为“希鲁格哆”。这个人就是被乌拉特人尊称为“喇嘛歌者”的三世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该文对梅日更葛根所做贡献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学理阐释。
段泽兴(内蒙古艺术研究所)从《内蒙古音乐文物大记———内蒙古卷》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中谈到,“此书是把流传于内蒙古所有音乐方面的文物分为乐器类、图像类提供给大家作参考,通过此书收录的文物可以进一步了解内蒙古地区丰厚的音乐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文物证实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如距今6000年以上的埙的发现意义极其深远。阴山音乐文化的概念很大,其中有许多文化现象是重叠的,其文化内涵及外沿的界定应更为清晰”。
张晓武(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论文《分析两首———“草原圣歌”从圣诗音乐创作作品看内蒙古环阴山地区基督教(新教)圣诗音乐本色化作品变化进程》文章中,例选了两首“草原圣歌”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出这一地区圣诗音乐本色化创作作品的特点以及在内蒙古环阴山地区地方音乐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和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圣诗音乐本色化创作的意义。
佟占文(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故事•表演•文本———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探微》一文中,对布仁初古拉演述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的故事及文本进行类型学分析,讨论了故事如何通过表演而生成文本的过程。认为,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故事类型,其表演按照既定的程式进行,文本是表演的结果,同时它是反映故事、考察表演过程的参照。
四、内蒙古地区乡土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创新研究
为了使内蒙古的乡土音乐资源能够转化为教育资源,使内蒙古的音乐教育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次会议特设了此方面的研讨内容,与会的专家们对此议题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使大家充分地认识到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就引进多元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达成了共识。
张天彤(中国音乐学院)首先传达了近期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的音乐学院学科建设会议的精神,并以《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为题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学科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在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中所取得的一些优秀成果。
金铁宏(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关于民族音乐教育的若干思考》的论文中强调:民族音乐艺术传流,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它作用于民族个体和群体;能使整个民族思想统一,情感融洽,意志集中。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项基本工程。
因此,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已不仅是音乐教育本身,而是对我们的新一代树立起健康的审美心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热爱中华民族,热爱民族的音乐艺术,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并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对于创造性地振兴中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崔东伟(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高校公共音乐课与民族情怀的培养》一文中通过对高校开设公共音乐课的作用、艺术教育与民族情怀的关系以及高校公共音乐课如何实践对大学生民族情怀的培养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为高校艺术教育的完善提出新的思路。
李书宇(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写在包头市中小学音乐教师骨干教师培训后的感想》的论文中提出:“我区有着非常丰富的音乐资源,我们可以尝试编写我区自己的中小学音乐地方教材。例如,二人台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二人台是内蒙古地区的重要艺术资源,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了许多其他音乐文化冲击。如今,在文化界人士的大力呼吁下,二人台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在我区中小学开设二人台课有利于强化学生民族文化学习的意识,更可传承我区民族优秀文化,并可提升学生对于民族、民间艺术良好的鉴赏能力。”在文中他还对提高教师培训的认识,对音乐教师培训的经费投入,提供更为广阔的继续教育平台等方面提出了良好建议。
张静(河套大学)宣读了其论文《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钢琴教育研究》,并在发言中谈到她参加巴盟河套地区阴山音乐文化教育课题组的工作情况,提出今后努力将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资源引入大学的课堂中的设想。
篇6
他们都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对他们来说,田野就在“那里”,他们就在“这里”。现在的“那里”,有农村空心化的偏寂;现在的“这里”,有城市集群化的喧嚣。“这里”可以给“那里”打手机、通商贸,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他们的呼吸不远的地方。然而这一“田”之隔,却有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他们需要掌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考察同时代存在的不同文化样式和文化概念,选择更合适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地方文化空间保留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得出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学术观点。
这样的艺术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包括可能产生新问题,对某些已形成思维定势的专业术语予以重新界定,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作出新的描述,乃至说服其导师级的学术同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成果便不以年资论,而视其能否用理论烛照历史,推进学科研究。
本书的作者孟凡玉博士正是这批年轻博士中的一位。他的田野在安徽贵池,他从那里“拿”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天,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来找我,记得那论文封皮上写了他的村社调查地名“荡里姚”三个字。这三个字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神经,而不只是“跳”入了我的眼睛。我收下了这篇论文,仔细地看,然后答应参加他的答辩会,现在又乐意为他的这本书写序。这期间,他花了六年时间修改论文,这种学风,我也欣赏。前辈都提倡“十年磨一剑”,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一位博士研究生,从学子到学者,也需要较长的蜕变时间。后来作者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比起专攻艺术学本身的学位,也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扩充知识,反观以往。而这段多出来的时间,正是作者重新解读和消化田野的时间,这样才能对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差异作出从容的解释。说实话,我与作者不大认识,六年来只见过一两面而已,但从这份成果本身来说,我们又似乎在理论上认识了很久。
现在需要具体而简要地谈谈这本书。本文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这样能解释作者所坚持的东西。这些东西含有田野地点的内在知识,又拥有当地历史与现代社会共生的宏观文化环境,因而其个性中必有共性。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有诸多可谈的共性问题的。不过,属于我的专业,适合我来谈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视角,从作者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过程中,提取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下,我重点就这方面谈谈这本书。
作者是一位艺术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按照他的排序,民俗学站到了艺术学的背后。而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联系,正是文化差异性研究的一种共性。当然,艺术学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关联,只要看看早期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著作,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史。况且在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中,还经常共用资料,共享理论和方法。以往各学科还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民间艺术是一座保存地方、民族、语言、宗教和音声的独特成分的富矿。在我国,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艺术学的民俗学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解放、文化宽松,在艺术学领域里,傩戏研究推进很快,钟先生还曾就傩戏面具研究与保护问题发表过文章②。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傩戏。傩戏研究是涉及戏曲、民俗、宗教、音乐、舞蹈、绘画和考古等多专业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有各行专家的多种发表成果。本书作者的田野研究在21世纪初进行,已有前人成果的厚实铺垫,可以提出更为深入具体的问题,而深入具体的问题才能上升为共性问题。
本书的书名是《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不用说,作者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安徽贵池的一个叫“荡里姚”的村庄。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个案法。他主要运用音乐学等艺术科学的理论,同时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对当地傩戏音乐的传承内容、形式、文本保存状态和传统地方音乐文化空间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尤其对个案点的傩戏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符号,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作者的田野作业不是一般的走过场,而是在田野定位、田野观察、田野关系、田野文本和田野研究等多个环节上,都把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贯彻得相当扎实。作为青年学者,他还将自己的专业志向和社会责任感都投入到田野中,一丝不苟地面对他观察的世界,也同时面对他所身处的多元文化组合的现代生活,这种个案研究便能成为全文研究的基础。
作者的观点是将傩戏音乐表演与地方民俗文化表演结合起来讨论而产生的。他以自己的导师薛艺兵先生提出的“仪式音乐”理论为基础,作了拓展研究。其实这种选题和研究路径不无冒险,但他能将自己的研究搭建在以傩戏音乐为主线的“村落文化空间”的资料系统上,建立了与导师不同的资料系统,这样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新视角。事实证明,他将薛艺兵的理论给“荡里姚”化了,这就在他的领域里完成了这项拓展研究。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说,在他的个案中,对“荡里姚”傩戏里长期传承的《孟姜女》剧本的傩戏音乐和民俗表演作了相当完整的调查研究,还对这部戏中的哩和装饰音乐作了精彩分析,这也给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孟姜女本来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经典题目,但从前它们关注的是孟姜女的文本,而不是孟姜女的戏曲音乐和民间宗教仪式。现在作者用音乐学理论之烛,照亮了这两个暗处,而且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都能接受,这就是从个案到共性的成功。
作者对自己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多层次、有分寸的交代,这也是严肃的研究成果所必备的一部分。
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如果是成功的,那就应该能够从中抽取出一般性的可资借鉴的东西,进而转为宏观层面上的讨论。我认为,根据作者的这本书,也结合考察其他艺术学科的同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类研究之值得关注,在于提供了三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一,仪式研究的文化价值。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看,艺术学所研究的民间艺术对象会被分为艺术的与非艺术的两大类,艺术学者要对其中的非艺术现象进行文化含义的研究。在一国艺术学中,这种文化便是民俗文化。对这种民俗文化要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其深处便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传习方式是仪式。有了仪式,才能招徒弟、念经文、作表演。仪式让地方集体不停滞地走进信仰世界,让他们将历史与现实灵活地融合,并产生能说服自己的集体性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仪式也是一个知识教育系统,它脱离于现代学校教育的体系之外,而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中。
现代学者已习惯于启蒙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多样化的、差异性的民间艺术说得自娱自乐、排忧解难、热火朝天,其实它们有时也很孤独、狭隘和寂寞。正是在这种地方,仪式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成为照亮艺术的一缕强亮的烛光。民间艺术的表演活动对于保存民俗、宗教和仪式而言,是精神传承,也是物质化行为,同时是初级均质社会组织的活动过程。在这些方面,仪式还起到流动性的链接作用,而这正是仪式所具备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第二,发现民俗知识的价值。从艺术学的视角调查研究民俗文化,容易把民俗当作“知识”处理,然后艺术学者往往使用变迁和发展的观点,对各种非直接用于艺术活动的民俗文化传承予以延伸解释。作者大量描述了“荡里姚”正月期间上演的孟姜女傩戏的整体演出过程,介绍了相关的家族、道士、科仪、日常器用和说唱文本,而这些描述和介绍无一不能脱离对当地的“知识”的解释。作者在艺术的背后找到了民俗,其实就是解释了这些知识。民俗学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民众本身解释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价值观同一性的科学。作者还提供了他本人在田野现场中换位追求、理解和反观这种民俗知识的发现过程,这就交代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经过与必要性。
当然,作者对民间社会的、非外来的、非艺术的地方文化活动是认同的,而这种认同又会使他的个案与文献有矛盾。而艺术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的特点,本来就不是没有矛盾的,作者的工作是站在个案与文献两者之上构建新的理论格局。更宽泛地说,艺术学的研究一旦进入民俗文化,就会多元,就会有差异,就会非均质,而艺术学者正确地描述这种多元、差异和非均质的文化现象,就能发掘艺术在民间的巨大生命力,增加艺术学的活力。
第三,用考古学的眼光将古老艺术当作所有古老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艺术学,毕竟以艺术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下田野,调查研究广大基层社会传承的民间艺术,发现了古老的艺术种类,艺术学者便容易使用考古学的观点,将这些古老艺术当作文物。这也使艺术学接近民俗学,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包括以艺术形式传承的“礼仪、风俗、行为惯制、迷信、歌谣和谚语”③。更早一点,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在167年前就已经这样说了。但是,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已经并不可信。我们要问:古老的艺术现象怎样以古老的传统形式不停滞地传承?怎样被地方群体加以新创造后转型传承?而这正是艺术学和民俗学在当代社会都要进行的工作。
第四,用民俗志的观点将文本化的历史文献放到日常生活中考察,补充民众对民俗表演的认知内容和地方民俗文化要素。我国傩戏文献缺乏,仪式音乐文献稀缺,但不是没有。这类文献一旦留存下来,也已经历了几百年或上百年的历史。要用田野个案的方法恢复历史文献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目前的问题是,田野调查者容易将所获得的历史上的音乐或戏曲表演文本当真,并将之作为文本化的民间文件去处理,甚至试图照样还原其在民间的表演活动。我们要说,这只是学者的假设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个案法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即历史文本与日常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由文本化过程中的复杂社会活动造成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有空间要素,空间要素不允许时间的任意延长。所以,我们在个案调查的空间中看艺术表演,对特定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而言,空间表演是有时间长度的,这个时间长度要符合该空间中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超过了这个时间长度,人们就要去休息,回到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中去。如果这时空间中的表演还在继续,那么剩下的是神的时间或寺庙的时间。本书的民俗主体是村民群体,当作者告诉我们,正月里村民出门看孟姜女的傩戏表演了,他们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散场,什么时候只剩下道士和戏班在没人看的时候仍在吟唱,我们就能感觉到,这里面是有外人与局内人对时空观念的理解的差异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现象和对艺术现象的实地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某些学者过度文本假设的批评。
现在谈谈研究过程。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说几句题外话。我在跟随钟敬文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里,体会到了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缘分。二十多年前,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得当时在答辩委员会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先生。在进行到古代民间艺术理论的环节时,廖先生曾问我,民歌的艺术传承是否存在其他独立因素,而不止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解释?我听了就明白,廖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出自他长期、复杂而深入的研究,而他在这种场合下提这个问题,还夹杂着他对一个研究生的学术期待,因而承载了、超越了研究生实际业务储备的巨大科研信息量。他是钟敬文先生的多年友好,钟先生了解他精通德文和中外音乐理论,熟悉德国的民俗学传统,他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艺术是有不一般的眼光和深度的,这也正是钟先生请他来的目的。数年过去了,钟先生和廖先生均已谢世,而我仍记得当年廖先生的直面和友善,记得他的问题。
我毕业两年后,开始协助钟先生编纂我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民俗学概论》④。在这项工作启动之初,钟先生圈定了一个以民俗学者为主的多学科作者团队,其他学科的学者分别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科技史学。艺术学小组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他对中国乐理、器乐和声乐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能,出书也多。他负责的那一组,除了他,还有专攻戏曲、舞蹈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其他学者,都是他请来的本行的“八仙”。这几位作者个个业务精专,都能遵守结稿时间,交稿很快,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乔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师大著名语言学家萧璋先生的女婿。萧先生是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口碑好,学问好,还擅长唱京剧,据说有精通音律的世传功夫。他的女儿是钢琴家,招了乔建中这位音乐理论家的女婿。钟先生派我到萧先生家去“搬兵”,萧先生果然满口答应,不过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我不用给他打电话,他每周一定来看我们,他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不来怎么办?万一他有事呢?不然您把他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 “我从来不打,他一定来,我没有他的电话。”如此“铁”的翁婿信任让外人无言以对。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钟先生和我都在私低下叫乔建中为“乔老爷”。他还动不动就送我们一本新书⑤,里面经常会写到音乐与民俗的关系,让我们看了很爽。这部教材写了八年,我们也与乔先生交往了八年,可以说,与乔先生的这段交往,直接产生了我国民俗学与艺术学交叉研究的教材成果。
本书作者孟凡玉的博士生导师薛艺兵教授,我是通过英国音乐人类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知道的。有一首歌叫《传奇》,我与钟思第的见面也可谓一段传奇。1994年的一个下午,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他。他像一般欧美学者一样开门见山,坐下来就问我在河北定县调查秧歌戏对民间音乐的看法。他还说,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合作,搜集了河北民间乐社的宝卷唱本,里面有文字部分,需要继续做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直到最后也没问他究竟是怎么找到我家来的。这种访问之奇特,让我见识了异国书呆子的风貌。他还给了我两个信息,一是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不能回避宗教,二是他有一个中国合作者叫薛艺兵,他很看重薛艺兵的才能和踏实的田野精神。以后,我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每到一处,都会偶尔与钟思第通信,他来信,我就回信,内容都是有关音乐与民俗表演的问题。我在英国时,他还邀我去伦敦大学讲课,我顺便参观了他的工作室,那里布满了音乐制作设备和光盘架,几乎没处下脚。1997年底,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听说薛艺兵就在香港中大学习,我便趁会议休息时间跑出去找他,但到了地点,人家又说他暂时不在,我只好退回。就这样,直到2007年参加孟凡玉答辩时,我才第一次与薛艺兵教授见面。不过说实话,因为有了钟思第,我们好像早就是老熟人了。
由于与乔建中和薛艺兵的关系,我又认识了张振涛教授。他们都是好兄弟,满怀学术理想,多年合作奋战,开辟了中国音乐人类学的一方圣土。他们当年取得的大批成果轰动一时,也影响长远。我曾把钟思第的遗憾说给他们听,他们便热情地介绍我去他们在河北易县开辟的田野调查点作民俗学调查。以后,钟先生和我合招的一名博士生就以这个村的宝卷文本为基础资料,撰写了民俗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在这个过程中,“钟思第”是我们经常谈起的名字。
按字辈论,孟凡玉当属新科派的艺术学学者了。现在,他的新著的出版,不免让人回忆起这段研究路途上的长长的队伍。我想借央视一个栏目的名称《文化正午》形容此时的心情,因为“文化正午”能忆旧,也能望远,而学术创新的过程莫不如此。
注释:
①孟凡玉著《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②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艺术观,参见董晓萍《钟敬文的民间艺术学思想》,《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2年第9辑,第39-53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出版。
③(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lo Valk)《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董晓萍译,收入朝戈金、董晓萍等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第70―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④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篇7
[1]陈建勤:《中国民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2]曾田力:《大众传播媒介中的中国音乐文化》,《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5月。
[3]陆小玲:《原生态民歌与大学生人文教育》,《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刘嵘:《原生态民族音乐与当代音乐发展研讨会侧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5]查子明:《中国原生态民歌生存发展之我见》,《音乐探索》2006年7月。
[6]俞人豪:《“原生态”的音乐与音乐的原生态》,《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
[7]米永盈:《我看“原生态”民歌——兼谈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社会纵横》2006年第12期。
[8]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
[9]郭声健:《艺术教育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薛雷:《“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再认识》,《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2]尹萍:《探索高校声乐教育中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源》,《高校探索》2005年第5期。
[13]乔建中:《传统能给我们什么?-关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再思考》,《中国音乐》2004年第4期。
[14]金兆钧:《关于“原生态”与“学院派”之争的观察与思考》,《人民音乐》2005年第4期。
[15]夏滟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16]徐士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版。
[17]王敏:《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亟待加强》,
参考文献
[1]安丽.在“民族”的土壤里发展”民族唱法”——对中国戏曲和湘西原生态音乐的思考[J].大家,2010(11).
[2]张敬忠.中国民歌在现代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从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与保护说起[J].四川戏剧,2012(4):82-83.
[3]李震.湘西原生态音乐的艺术价值及素质教育功能[J].音乐天地,2012(5):4-6.
[4]陈业秀.地方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的艺术教育价值与实现——以台州特色民间音乐课程资源建设为例[J].教学研究,2009,06:62-65.
[5]崔学荣.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D].福建师范大学,2010.
[6]赵国宏.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7]张丽华.网络音乐教育资源开发与整合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4.
[8]李芝.论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文艺生存空间的拓展[D].广西民族大学,2014.
[10]吴小丽.原生态音乐文化分析——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待原生态音乐文化的发展[J].戏剧之家,2009,(04).
篇8
一、专家发言内容精辟、观点深邃
张振涛在《背谱》中认为,工尺谱的骨干音记谱方式促使乐师不得不采用费时费力的方式,死记硬背,乃至再次转记,即民间艺人在谱本的“大字”之间,填写只有学习者自己懂得的“小字”和各种各样的奇怪符号的方式。这个有悖常理的现象,体现出隔离文人与乐工的知识系统双轨制。张青在《地方戏的内核塌缩――以国家级“非遗”淮剧为例》中总结了地方戏内核塌缩主要表现在区域人群通过地方戏所反映的审美趣味被否定,地方戏原生区域人群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被质疑,区域戏曲文化的典型符号被剥离,在地方戏中体现的“群体情感记忆”被抹去,最终导致群体文化自信力被剥夺。张伯瑜在《要保护传统,请不要改变它!》中主张“非遗”所面对的传统音乐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其中不仅仅是声音问题,还与人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的变革必然带来生活的改变,生活变了,附属于生活的音乐能不变吗?钱茸在《唱词音声解析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研究的关系》中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重点之一是地域性文化遗产,中国音乐的地域性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声乐传统,且与各地域方言音声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杨殿斛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中论述到当下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壮大,应和了“非遗”保护的国策推行和文化建设的国家主张,这些政策成就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时代风景。
杨曦帆在《区域音乐研究实践》中指出对背景文化的整体解读,区域研究对民族音乐学之所以有效,还在于几乎所有民间音乐或多或少因地域、历史、人口等等原因而大致和文化区域相关。赵向欣《豫南花鼓灯的研究、传承与发展》谈及豫南花鼓灯作为信阳民间歌舞的主体,它在对本地其他文化形态施加影响并在区域文化特性认同充当民间文化与情感交流的介质,体现汉民族创作天赋等方面,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在《光山花鼓戏的文化归属》中指出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养成了信阳民间音乐文化独具特色的风格,但在研究信阳、光山民间文化时也不能忽视其在形成过程中兼容并包,上承中原,下联吴楚的一面。戎龚停在《沿淮民间歌舞的时空构建脉络》中认为,沿淮民间歌舞是一支庞大的歌舞体系,是在与多项民俗的共融生发和相依滋养的历时进程中而构建的,具有多重层次的生态共生模式。马志飞在《淮河流域传统曲艺的传承谱系与美学品格》中认为淮河流域的传统曲艺不仅具有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过渡性文化色彩,还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和美学品格,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和文化交融等因素造成的。喻林在《淮河流域花鼓灯音乐的道家文化阐释》中强调淮河流域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流行于此地的花鼓灯艺术也深受道家文化的浸润,主要体现在“通神警人”的价值观、“自然无为”的审美观及“世俗娱乐”的功能观。
周显宝在《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之互育共生――人文地理学视野中的皖北仪式音乐研究》中指出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观念、行为和人文景观及其互育关系的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杨传中在《多学科视角看花鼓灯歌舞艺术中的文化》中强调花鼓灯歌舞艺术是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重要品类,兼具舞蹈、灯歌、锣鼓与后场小戏表演等诸种表演样态,从多学科进行研究将得到很好的阐释。杨民康在《从北方秧歌的生存现状看当代传统乐舞文化变迁的几个特征》中根据近十余年来在北方秧歌展演等地进行田野考察的经历,对该类乐舞展演活动的当代文化变迁状况予以研究和分析。
秦序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通过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概念进行解读,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论述,对学界中关于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读进行了相关诠释。傅利民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的思考》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是个永恒的话题。孙云的《俗曲佛用――以五台山佛教为例的微观解析》认为拿来世俗音乐为用是佛教音声创作的主要传统,进入佛教音声体系的世俗音乐一部分与经文中的偈赞结合,其他成为仪式专曲和供养曲,唱经、伴奏、供养是其为用的三种功能样态。李清的《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认为这是一套一钟一音的编纽钟,只有正鼓音的音列,整套石磬由于毁坏严重,虽有一定的音律组合,但无完整的音阶关系。
二、采风、研讨、表演三位一体
大会在信阳市罗山县周党镇龙镇村罗洼组李世宏皮影基地设置了第二会场。专家们参观了皮影工作室、皮影戏戏台、皮影藏品陈列厅等。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纪华林、陈依雯、郭德华、金平、于立刚、刘世嵘六位教师分别做了题为《走进课堂的豫南花鼓灯》《浅谈豫南花鼓灯文化的传承》《淮河流域戏曲音乐的实证研究》《罗山皮影戏的发展历史及传承机制研究――以李世宏皮影基地为例》《信阳新县“三壁吹打乐”音乐文化特征分析》《淮河流域花鼓灯艺术表演形式的比较研究》的发言。
研讨会后,与会专家在皮影基地大院欣赏了由李世宏和王晓丽一起表演的传统罗山皮影戏《文武魁》。表演结束,专家针对演出中的楔子全集、曲牌集子、大板词等唱词和主打腔调“西调”“扑地哼”调和“南调”进行了记录。在采风现场进行学术研讨是此次大会的一个亮点,这使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与民间活态紧密结合、相得益彰,让书面历史与当下传统对接,有较强的实证性和现场感,让历史、传统、田野三者相互比较、印证。
篇9
中图分类号: G6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9-0061-01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孕育了八千年的音乐文明,在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无数优秀的璀璨文化,其中民间歌曲就是一颗闪亮的明珠,闪耀着与众不同的光芒。民间歌曲把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感情,诠释的淋漓尽致。在民间歌曲的体裁中,号子、山歌、小调是最基础、最典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以俭朴生动的艺术形式,丰富淳朴的表现内容,活跃在人民的生产生活当中。
在现实生活中,某种民族歌曲和某些地区的民间歌曲等名词出现时,经常会有含糊不清或混淆的现象,像“维族歌曲”与“新疆歌曲”,“信天游”与“山歌”,在大不分人们的印象中都是同一个意思,其实这种叫法是不专业不正确的。那么,民间歌曲和民族歌曲有什么区别?
一、中国民间歌曲的起源
民间歌曲是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它源自中国原始乐舞,原始乐舞是最古老的歌、舞、乐三者结合的形式,民间歌曲含有原始乐舞的遗留成份。原始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在生产劳动中通过模拟动作来进行狩猎、游牧、战争以及爱情,逐渐形成了原始乐舞的雏形。
民间歌曲从原始艺术萌芽发展而来,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的反映。自古历代皇帝与王公贵族们经常通过采风把民间歌曲加工改编为宫廷歌曲,使得民间歌曲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愈发的完美和成熟起来,《诗经》、《楚辞》无一不是民间歌曲的总集。各种民间音乐艺术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民歌,包括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等,无不从民间歌曲中汲取营养和素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民间歌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触,像:敬酒歌、哭嫁歌、洗衣歌、采茶歌等等,它们那淳朴的表现风格,热情生动的表现形式,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当之无愧的音乐艺术之基础?。
二、民间歌曲的概念
周青青老师对民间歌曲的释意是:“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因此,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情感体验,日臻完美,成为人民群众思想情感表达的结晶。”音乐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对民歌感兴趣的人在不同的书籍、著作、论文当中,在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深度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更大的拓宽了人们了解民间歌曲的途径,也使得民间歌曲方面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
我认为民间歌曲,就是源自民间的歌曲。它是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诸多歌曲艺术形式的来源,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劳作过程中诞生,由劳动人民直接创造,具有鲜明的人文风俗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状况,并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注入新的成份的歌曲形式,表达着人们最真实、最淳朴的情感,并有着独特的歌曲风格和地方特色。它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来源,并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口头传承的一种传统歌曲形式,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同时又情贯古今的艺术,是歌曲中的一颗“活化石”。
三、民间歌曲的特性
1.继承性。民间歌曲保存着历代生活的形象特征,积淀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因素。它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民俗活动紧密结合,世代相传,不断发展。
2.大众性。它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自娱性。它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自人们心中最真挚的情感流露。
4.即兴性。它歌唱方式规范性不强,歌曲唱腔因人而异,随情而发。
5.适应性。它是以历史时代为背景,适应着潮流与发展,有着与时俱进的特点。
6.地域民族性。它受地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和地域文化色彩。
7.口头性。它是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且口耳相传的歌曲。
8.变异性。民间歌曲的曲调和歌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而有所变化。
四、中国民族歌曲的概念与特性
民族歌曲作为反映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民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性歌曲,这种在自己民族当中流传和发展的歌曲,就是民族歌曲。从狭义上讲,一个民族特有的或专有的歌曲形式,就是民族歌曲。民族歌曲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人文秉性和民族特质。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地理、气候、环境、习俗都各不相同,每个民族受这些因素影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歌曲风格。
五、中国民间歌曲与中国民族歌曲的关系
在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聚居、杂居、交错居住的情况很多,日常生活中,民族一词习惯上多指少数民族。因此,民族歌曲也常指的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相应之下民间歌曲就成为汉族民间歌曲的代词了。
其实并非如此,民间歌曲自己就是一个庞大的歌唱文化系统,它本身含有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反过来说,民间歌曲是由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性质、不同风格的歌曲所组成的,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并不是两个毫不相连的整体。正相反,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两者的含义虽不相同,但却同属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56个民族的风土人情,交织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歌曲文化,其中每个民族又以自己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风貌、人文景观、生活习惯,孕育出多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
在我们明确了民间歌曲和民族歌曲的概念与关系之后,可以得知,民间歌曲是一个庞大的歌唱文化系统,它含有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同时民间歌曲又是民族歌曲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却并不矛盾。所以,当听人们把“新疆歌曲”叫做“维族歌曲”时,就可以判断这说法是不正确的。“新疆歌曲”严格地说,它包括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族民间歌曲。
结论:
中国民间歌曲形式多样,且生动优美。在民间流传的各民族歌曲都受大众的喜爱,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民间歌曲是一个大的歌曲范围,指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民族歌唱形式。民族歌曲指的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各种具体的民族歌曲,两者含义虽不近相同,但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歌曲中一些不适应时代精神的部分,会逐渐消失,而歌者们又会把新的认识和时代精神融入其中,使民间歌曲富有时代感与生命力,附和着时代跳动的脉搏。
我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可以让大家对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的认识与了解更加清晰。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运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使其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湖南益阳;民间礼俗;仪式音乐
 购物车(0)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