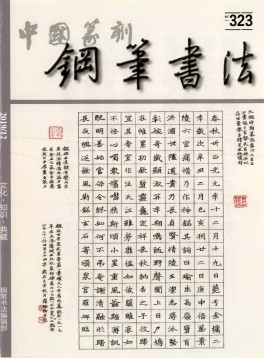期刊在线咨询服务,发表咨询:400-888-9411 订阅咨询:400-888-1571股权代码(211862)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模板(10篇)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1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
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2
【 正 文】
“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具有原创意义,它既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定,又是这本质规定的由来。
一、体验的世界与世界的本真
中国古人的世界建立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情感体验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古代艺术在这样的世界中形成与发展。
1.“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性
从艺术文化学的角度说,文学艺术从属于文化并规定于文化,因此,阐释“情”的文化原创性,同时也就是在揭示“情”的文学艺术的原创意义。
原创的含义不仅在于本质规定,更在于本质生成。把“情”提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创位置,是指认中国古代文化的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
缘“情”而生,是说中国古代文化是其先民及后来者情感生活的产物。这涉及生存论及文化学的基本问题,即中国古人的生存就是情感体验的生存,中国古代文化也就是情感体验型文化。
把中国古代文化指认为以情感体验为特征的文化,这可以说是百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化学研究与生存论研究在不少学者中日渐取得共识的一个基本观点。如中国现代较早的文化反思者之一梁漱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体验,提出中国传统生活与传统文化的重心在于“家”,在于“家”所特有的情感关系,由“家”的情感关系扩延至社会,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喜欢斟酌情理情面”的生存特性(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8页。)。他这是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情感的寻根,并把这根确定在“家”的血缘情感上。林语堂在分析中国文化精神时,对比中国与英国民族文化的异同,也得出结论说:“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说中国文化,本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并没有难懂之处。”(注: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引自《中国文化概论》,第195页。)林语堂所说的“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这正是中国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以人情为前提”,便是体验的文化特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的当代学者张岱年,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四个要点,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及天人协调。细究他这四个要点,会发现这些要点的形成,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具出于重行为目的、重行为反馈、重行为体验的实践理性,直觉体验及情感体验是其基本理性特色。李泽厚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提出一个“乐感文化”的命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概括为“乐感文化”,以此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他对此概括说:“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识逻辑的清晰。总起来说,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李泽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乐感”型、审美型的概括,正是突出了这一文化的情感体验的本性。我在《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一书中,曾专题分析过这个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的本体特征概括为情感体验特征,并分别对之进行了文化特质的、文化思维的、文化哲学的及艺术论的思考(注:拙著《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2.“情”的本真规定
先考察一下“情”的字义。“情”,《说文》:“人之阴气,有欲者。”按阴阳说,阴阳为生命之本并化生人的万有万能,说“情”为阴气,这是将“情”推到了生化生命的本真之处。段玉裁注,情乃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欲,是生理自然需要不学而能,这又是将“情”归入人的本真状态。《吕氏春秋》强调“情”的天生自然:“欲有情,情有节……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吕氏春秋·情欲》)这是在确定“情”的生命自然即直接的感官根据,是耳、目、口对声、色、味的自然欲求。“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然又是这生命活动的本真。《尚书》“情”有一见:“天畏fěi@①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孔安国《尚书传》对这一“情”字作“人情”解,即民群的真实感情,“人情”被看作天是否辅助的尺度。此后,“情”便与事物之真、实相关,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关。“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左传》庄公十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鲁有名而无情”(《左传》哀公八年);“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国语·鲁语上》)。这“情”,都是事物、事情的真实情况。《论语》用“情”两处,都与人的自然本真相关:“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
因为“情”本义于生命本真状况,所以它常与另一个表生命之本真的字“性”连用,称为“性情”。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这“天”便是自然,自然天赋。荀子提出“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情”是自然天赋的本质,是生命的本真。荀子之后,“性”、“情”、“欲”三者关系的哲学之思也就逐渐多起来,形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辩——“性情”之辩。
中国古人热衷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本真追问,把本真作为文化建构、艺术实践的基点或出发点,并在本真追问中把握判断事物及行为的标准。如儒家先哲孔子与孟子,在推衍他们的人世之道与道德之天时,便从本质设定出发。“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羞耻感在这里被推为不言面喻的本真标准;“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情”被指定为“性”本善的根据;“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这是孟子对羞耻感的进一步的本真强调。管子本于“情”的人事道德推衍更为直接,“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管子·禁藏》);“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管子·君臣上》)。道家进行的道德推衍其实也本于“情”,与儒家对“情”的人世社会比附与推入不同的是,道家本于“情”却比附于“自然”,再由“自然”而推入社会人生;当然,道家对于“情”的本真设定或本真理解也不同于儒家,道家更强调“情”的自然性。“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无情不是否定“情”而是不动情,这里有一种超越喜怒哀乐的更为广博深厚的“情”,这便是宇宙人生之自然,是融于宇宙大道的生命冲动。至于墨家的“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墨子·亲士》);法家的“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韩非子·难三》)等,也都可以看出他们按照各自的“情”的本真理解,进行各自的“情”的本真推衍与强调。
二、建构体验世界的心灵方式
在中国古代,本真之“情”涌发本真之欲,本真之欲又实现于本真的血缘亲情关系。血缘亲情关系是“情”的本真关系。由此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便也可以说是充分社会化的血缘亲情关系的意识形态。而建构、接受、运用这样的意识形态,又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这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必然也是血缘亲情关系型的。所谓思维形态的血缘亲情关系型,即它与血缘亲情关系共同发生与发展起来,它以血缘亲情关系为思维对象,在对血缘亲情关系的思维中不断完善这一思维结构,并思维地解决社会化的血缘亲情关系的各种问题。对这一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我在《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一书中,曾将之概括为情感关系思维或情感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①客观的感情依据;②思维主体现实体验向感性对象的融入;③过去经验对于现实感性对象的渗入;④表诸于形象或含有形象因素的一般判断形式(注:拙著《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在这样的思维形态中,“情”有了本真之外又一重原创意蕴,即它是中国古人建构与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经由这样的思维形态,中国古人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有直接的关联——社会文化活动直接关系着艺术活动,艺术活动也直接关联着日常社会文化活动,甚至不少时候,社会文化活动就是艺术活动。
且看《吕氏春秋》这段话: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叹,有进乎音者矣。大飨之礼,上玄尊而俎生鱼,大羹不和,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吕氏春秋·适音》)
由音乐而民俗民风,由民俗民风而理义之行、国家之治。对这段文字的解读,不仅要注意它指出了艺术与人伦政治的关系,更要注意它对于艺术与人伦政治的情感关系的揭示,它们面对同一的情感关系,把握同一的人伦情感世界,所以它们才能由此及彼地互相指认互相通达。艺术与人伦世界的同一关系,在孔子论诗、庄子寓言、韩柳论文中都被作为通则而运用,这不是他们对于艺术的误解与偏见,而恰恰是他们对艺术与现实生活情感思维同一性的深悟。
对“情”的思维形态意义,中国古人多有论述。如《淮南子》,从“情”感物而生并形于外的方面加以揭示:“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淮南子·缪称训》)汉代从石渠阁奏议到白虎观奏议,涉及“情”的思维规定性,并以此作为制定国家等级制度的根据:“情性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诀》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白虎通德论·情性》)这指出情是阴化、静也、贪也、利欲也;性为阳施、生也、理也、仁也,二者在生存的心灵活动中各有所重,各有其活动特点,又相辅相成地展开心灵活动的过程。东汉王充基于情性阴阳之说,指出要更好地运“性”用“情”,就必须注意对之制约与调节:“故厚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论衡·本性》)这实际上是揭示了礼乐乃“性”、“情”思维的结果,因此礼乐才能反转来制约与调节性情。刘勰基于“情”的过程性理解,进一步作了“情”的艺术思维的揭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这指出“情”组织文学语言,使之由隐而显的表现功能。“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这是揭示“情”的文学发生过程。“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这是在讲“情”与艺术想象的关系。
体验情感型思维形态关注现实与历史的各种情感关系,包括人与人的情感关系,人与社会的情感关系,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长于对这类情感关系进行丰富复杂的情感体验,并以真切细腻地表现这类情感体验为思维目的。这一思维的艺术成果便是创造出生动地表现各种情感关系与情感体验的艺术形式。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在进行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古代美学的对比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古希腊美学也并不否认艺术对人的情感的影响和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它更为强调的毕竟是艺术对现实的再现的认识作用。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首先是艺术的情感方面,它总是从情感的表现和感染作用去说明艺术的起源和本质。这种不同,也分明地表现在东西方艺术的发展上。”(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由此可见,“情”确实是中国古人情感关系地建构与把握世界(包括艺术世界)的思维形态与心灵方式。
三、创生艺术的母体
强烈的抒情要求形成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的明显差异。突出的抒情特征的形成,则源于中国古代文艺史中抒情艺术的早熟及对于各种文艺形式的创生。
中国古代最早形成自觉并走向成熟的艺术是音乐,音乐的抒情本质早已不言而喻。
固然,不仅中国,在世界艺术史中,音乐也是出现最早的艺术,这已被很多学者认同。不过,最早出现的艺术与最早形成自觉并走向成熟的艺术并不是一回事。
《周礼》有一段话,证明至少在周初,音乐的创作与应用便已进入自觉阶段:“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②、大武……”。(《周礼·春官·宗伯》)尽管有资料证明,“礼”的观念周初已开始形成,但“礼”在当时生活中的作用却无法与“乐”相比。“乐”所感受并表现的秩序与和谐进一步理性化,才明确为“礼”。“礼”是规定了的秩序与和谐。对此,中国古人早有认识——“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乐”先于“礼”又通于“礼”,“乐”、“礼”共同规定与生发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乐”、“礼”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情感体验与情感理性形态,滋润与繁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抒情特征。
而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早熟,也证明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情”的根基。
中国古诗“情”的根基与“乐”相通,中国古代文艺史不乏诗乐舞原本一体的记载。如刘勰说:“或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文心雕龙·明诗》),孔颖达说:“大庭有鼓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昔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诗谱序正义》)诗生于歌舞,亦即诗生于“情”。
“乐”与“诗”这类抒情艺术在中国古代率先自觉并成熟,在于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根基——人伦情感的艺术形态,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感召力和普通有效的接受效果,使统治者与施教者把它们用作人伦教育的得力手段。中国古代抒情艺术率先发展与自觉,是人伦文化建构的必然。这个过程中,孔子以“乐教”、“诗教”为核心的艺术观同时也是文化观,起了重要的理性指导作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对此作过分析,透视了其中血缘亲情的文化根基(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很有说服力。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根基于中国古代人伦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伦情感本质就自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由于“乐”、“诗”抒发人伦情感方面很早便自觉与成熟,也由于孔子的理性概括与引导,使的“乐”、“诗”的“情”的本质规定成为后来因“乐”、“诗”而生发的其他门类的文学艺术也获得了“情”的本质规定。
四、文论诸范畴的总领
文论是文学实践的理论形态。“情”的文学艺术的原创意义体现在文论中,则在于它具有范畴总领意义。也可以说,“情”的文论诸范畴的总领意义,正证明它的文艺原创性。
“情”的范畴总领意义可以从思维形态、文论范畴发生及范畴构成角度加以论证。
①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都是情感体验思维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成物,分有情感关系的本体属性并运用与发展着情感体验型思维。所不同的是,文化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创生与建构,由于社会实践的物质规定性,情感体验型思维常因实践对象的客观定性而难以充分施展;即是说,对象的客观性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它否定体验的主观性。这时,活跃的便只能是主体的认知而非主体的情感。在文学中,对象的客观定性消融于文学创作主体,情感体验的特征性思维有了充分实现的条件。充分实现的情感体验思维,创造着情感体验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形成与之相应的文论范畴。由此说,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也是情感体验型思维的产物,是这一思维形态的理性成果。“情”在情感体验型思维中具有发生、运作、课题与衡定意义,“情”的生理与心理规定直接成为思维规定。作为范畴的“情”正以文艺的情感活动为对象,以揭示情感活动规律为旨归,因此,“情”范畴的研究也是情感体验型思维本身的研究。文论其他范畴孕生于情感体验型思维,所以也正在“情”范畴的研究之中。换句话说,“情”的情感体验型思维研究自然蕴含着文论其他范畴的研究,而且在文论其他范畴的研究中处处见出“情”的规定。
就拿“理”来说,在西方,“理”与“情”是对举的两个范畴,它们经常在二元对立的情况下运用。在中国古代文论,“理”却是“情”的构成范畴,“理”主要是揭示“情”的发生、运作及表现根据。如刘勰所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叶燮所说“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原诗·内篇》)等,都是在讲“情”、“理”相一的关系。李泽厚则把这种“情”、“理”相一相融的关系概括为“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国的智慧”(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11页。)。
②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都是“情”的生发
如前所述,最充分地体现“情”的本体意义的艺术是乐与诗,乐与诗的最先自觉与成熟,决定了它的理性形态“情”范畴是最早提出的艺术论与文论范畴之一。
《国语》记载周王与单穆公、伶州鸠关于声乐与声乐接受效果的对话,虽没有直接就“情”字展开,但二人由声乐大小、强弱、疾缓作用于感官引起的体验与感受的分析,及对这种微妙、复杂的体验与感受所唤起的道德感与所引起的道德行为的分析,都已深刻涉及情感心理学内蕴,都能从中看到较丰富的情感唤起与情感运用的经验(《周语下》)。《国语》还有一段“情”与“文”的对话,涉及“情”、“貌”、“言”的关系:“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赢氏。……(宁赢氏)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国语·晋语五》)这段记述提出了“情”与其外部表现相合相离的问题,也涉及“情”的话语表述问题。这类问题对此后的“情形”、“情言”、“情貌”、“情理”等艺术论与文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此后文论众多范畴课题的提出与展开,如“诗言志”课题、“性情”课题、“形神”课题、“神思”课题、“比兴”课题、“象”与“象外之象”课题、“旨味”课题、“虚实”课题、“言意”课题、“意境”课题等,无不与“情”的文学发生意义、“情”的范畴延展意义密切相关。
“情”对于“志”、“礼”、“性”、“心”、“德”、“神”这类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基本范畴的发生意义,更可以由孔子及其后学对于《诗》的多元解释见出。对艺术深有造诣的孔子,对《诗》却经常作非“诗”的解释,这类解释看似出格,其实,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以情感体验思维为特征的,文化系统的众多方面、众多范围都与“情”相通,可以互相生发彼此转化,就会少一些大惊小怪,这类解释只是顺“情”成章。如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致,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治《齐诗》的匡衡总论《风》诗时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这都是在强调艺术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情感同一性,艺术与各种社会活动都是“情”的生发。这一点在《毛诗》序中说得更为清楚也更为具体。如《召南·草虫》序,说这是“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郑风·将仲子》序则说是“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这类读解,不管距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是近是远,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孔子以降,确有很多哲人与文论家悟及“情”在生活中在文学与文论中具有重要的发生意义。
③“情”对文论诸范畴的构成
“情”对文论诸范畴的构成,是指文论诸范畴都合于“情”的定性,都分有“情”的性质。由于文论范畴为数众多,无法逐一分析,这里只能举诸范围之要,择几个基本范畴,进行“情”的构成性阐释。
a.“意”与“情”
“意”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它是文学创作的所欲表达,文学作品的已然表达,文学接受的理应获取。
“意”的提出与运用由来已久。《易传·系辞》中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此说法后来广为引用,它不仅提出了言、意、象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意”不可尽言的属性。《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又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些说法都认为“意”是有一定认知内容的心理活动,它要经由语言而表述,但语言又无法对“意”充分地表述。
陆机大概是最先在文论中运用“意”范畴的,他的《文赋》可以说就是为了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问题而作。此后,范晔的“情志所托,以意为主”(《狱中与诸诸甥侄书》);杜牧的“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答庄元书》);邵雍的“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论诗吟》);刘熙载的“意在笔先”(《艺概·文概》)等,都非常强调“意”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但也都认为虽则“意”之于诗文绝对不可或缺,但诗文又难于尽“意”。“意”的无可尽言,是中国古代文论对于“意”范畴的普遍看法。
那么,“意”为何物?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却又言说不尽或言说不清?对这个问题,范晔的一段话说得很精当:“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狱中与诸甥侄书》)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范晔从“意”的心理发生角度体悟到,“意”乃“情”与“志”的统一,是创作主体有感于生活而形成的“情志所托”的体验,这类“情志所托”的体验酿成具体的文学创作之“意”,这“意”便是具体化了的“情”、“志”融合的心理活动。“文”不能尽“意”,在于构成“意”的“情”的活动变化极为微妙,“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狱中与诸甥侄书》)对“意”的“情志所托”的心理发生过程,范晔之前的陆机曾进行形象地描述,揭示了“意”发生的感官依据,在“意”的发生中有“志”的萌动,有“史”的感悟与“文”的陶冶,而这一切又都涌荡“情”的波流,这才“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文赋》)。
正是情感体验的浑然而动和微妙之动,正因为“情”包融着感性、心志、既往的文史修养与现实的情境激发,这一切都难于为语言所分解所确定地指认,这就决定了“情志所托”的“意”的非尽言性——“意”的非尽言性来于“情”的构成。
b.“风骨”与“情”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高标准追求,也是很高层次上被运用的鉴赏与批评标准。
“风骨”的不易求,一个重要原因是“风骨”意蕴的不易把握。这种不易把握与“风骨”追求所必然伴随的“情”的活动分不开。“情”一经融入,大量无可言说的东西便活跃起来,更何况“风骨”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体验,就是一种情感体验效果。与构成抒情作品内容的情感不同,“风骨”的情感体验是对于作品的情感体验内容所进行的表现的体验。
因为“风骨”是对一定内容的表现情况的体验,所以有“风骨”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范畴(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风骨》、寇效信:《论风骨》、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都持“风骨”乃内容与形式的说法。);也有学者注意到“风骨”的情感体验性质,把“风骨”理解为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注: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65页。),并将之纳入道德规范。
宗白华曾深入地研究“风骨”,他的看法被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论者所引证。这里且把宗白华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摘引如下:“我认为‘骨’和词是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它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想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注: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这段话确实指出了“风”从情感中来,“骨”从思想中来这一层意思,但从什么中来并不意味着这来者就是什么。说“他从家中来”,这来者是他而不是家。这是简单的类比。“‘风’从情感中来”,“风”未必就是情感或情感倾向。“骨”也是一样。
那么“风”、“骨”是什么?还是前面那句话,“风”、“骨”是对于情感体验内容所进行的表现的情感体验。所表现的情感体验内容自然含有一定的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自然也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在其中,但宗白华并未止于此,他强调的是如何表现这一定的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他分析刘勰的“结言端直”,说这“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辨”;他说“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毫无疑问,这都不是说表现什么而是说如何表现,是就表现特点与表现效果而言。
从中国古人长于进行的类比思维来说,他们总习惯于把某种言说不清的属性、功能、效果等通过形象比喻加以述说。这种类比思维的要点在于被述说的东西与用来述说的东西,必在比与被比的基本点上能唤起认知与体验的一致性。“风”取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性类比,当是自然流动,无所阻碍。“骨”取于人或动物的机体之骨,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性类比,当是坚实鲜明,刚正硬朗。不管对“风骨”的具体内容做出多少解释,都应该就类比的基本特征展开。刘勰“风骨”论的意蕴正是在如是的特征性中展开的,“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guī@③璋乃骋。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文心雕龙·风骨》)。这些类比的精言妙语,确乎有些扑朔迷离,但根据类比思维的一般规律,抓住基本的类比特征,仔细地思索与体验进去,则不难发现,“风”者确实讲的是情感抒发所达到的自然流动、无所阻碍的表现境界;“骨”者确实讲的是思想阐发所求得的坚定鲜明、刚正硬朗的表述效果。不过,无论情感抒发达到的表现境界也好,思想阐发求得的表述效果也好,都是共见于表现的;而且,对这种表现境界或者效果的追求与接受,又都依凭于情感体验。
既然如此,既然“风骨”是以其表现性而见于情感体验的范畴,“情”对这一范畴的构成性,当毋庸赘言。
④“味”与“情”
“味”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范畴。这一范畴的文论意义存于文学文本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是在这接受关系中读者对文本所形成的读解感受。对这样的读解感受,出于类比思维,中国古人觉得这就像嗅到或尝到的令人陶然的美味,“味”便于读解感受联系起来,成为这类感受的指代,“味”也便逐渐被用做文学与文论的接受范畴。
最早取譬于“味”者,大概是《左传》载晏子论“和与同异”(《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以“味”喻一种特殊的音乐接受效果,即“声乐如味”。这种接受效果来于音调与节律的相成与相济,亦即和谐,产生的直接接受效果是平心,进一步的效果便是和德,即协调人伦之序。由这段最早的取譬于“味”的文字,起码能找出“味”的三点规定:“味”生于“声”与“听”的相互作用中;“声”被“听”而得“味”,又并非所有的“声”都能有“味”,有“味”之声必是音调节律相成相济之“声”,这是被接受的艺术一方的规定;“味”的接受效果,是接受主体的平心和德。再进一步分析,合于这三点规定而成“味”,就在于被“味”者能唤起一定的情感体验。为什么把这接受的规定确定于一定的情感体验?可以拿出三点根据:首先,音乐作为特殊的艺术门类,就是情感体验的艺术,它无法表述更多的认知内容,它是通过声音变化唤起情感体验,所以,产生“味”的这种“声”与“听”的相互关系就是一定的情感体验关系;其次,“声”被“听”而得“味”,这能“听”出“味”的“声”其实就是能唤起某种情感体验的“声”,“声”的唤情作用,不同“声”的不同唤情效果,当下心理学已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声音唤起情感的生理根据;再次,“味”的接受效果,即平心和德,也是情感体验的效果,根据情感心理学,和谐音乐的接受,可以平和焦虑、放松紧张,主体可由此进入安适宁静的心境,这正是情感效果。可见,“味”的最初提出,便是意指情感体验的接受过程与接受效果。
此后“味”被引入文学与文论,它的情感体验性质也就一并被引入。文论中经典的“味”论者有三人,即刘勰、钟嵘、司空图。此三人谈“味”都不离开情感体验,也可以说,对他们的“味”论都应作“情”的理解。
如刘勰说:“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文心雕龙·物色》)“入兴贵闲”,“析辞尚简”,讲的就是由“文”而“味”的唤情规定。钟嵘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这里的“兴”、“比”、“赋”不仅被视为作诗的基本手法,这同时也是手法对于相应内容的要求与规定。“兴”与“比”表现“意”与“志”,“意”与“志”都是一定的情感体验,这情感体验生发于“物”,“物”又靠“赋”而入诗,所以诗的“比”、“兴”离不开“赋”。作诗的关键就是协调“兴”、“比”、“赋”三种手法,即所谓“宏斯三义,酌而用之”。这样,“味”的接受效果就可以求得,即使“味之者无极”。可见,钟嵘的“味”同样是情感体验的接受效果。
司空图谈“味”更恍惚一些:“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tíng@④蓄、温雅,皆在其间矣。……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与李生论诗书》)在司空图看来,“味”是一种难于指陈的接受效果,“味”具有超象超知的接受性。超象超知又有所接受,司空图便把“味”更充分地交付给情感体验,因为从心理接受根据而言,惟有情感体验才能超象超知甚至超验地接受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微妙信息。对此,国外的格式塔学派、瓦尔堡学派及现象学心理学派已多有揭示。司空图当然未达到这些当代心理学的专门程度,但司空图凭丰富的艺术经验对此却有所感悟。至于司空图此段文字所提出的单一之“味”与调和之“味”的差异,对调和之“味”作的“醇美”及“味外之旨”的赞美,则是对“味”的情感接受关系及情感体验进行了更细微的区分,提出了更高的情感体验要求。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非下加木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3
“情”在 中国 古代文学 艺术 中具有原创意义,它既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定,又是这本质规定的由来。
一、体验的世界与世界的本真
中国古人的世界建立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情感体验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古代艺术在这样的世界中形成与 发展 。
1.“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性
从艺术文化学的角度说,文学艺术从属于文化并规定于文化,因此,阐释“情”的文化原创性,同时也就是在揭示“情”的文学艺术的原创意义。
原创的含义不仅在于本质规定,更在于本质生成。把“情”提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创位置,是指认中国古代文化的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
缘“情”而生,是说中国古代文化是其先民及后来者情感生活的产物。这涉及生存论及文化学的基本 问题 ,即中国古人的生存就是情感体验的生存,中国古代文化也就是情感体验型文化。
把中国古代文化指认为以情感体验为特征的文化,这可以说是百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化学研究与生存论研究在不少学者中日渐取得共识的一个基本观点。如中国 现代 较早的文化反思者之一梁漱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体验,提出中国传统生活与传统文化的重心在于“家”,在于“家”所特有的情感关系,由“家”的情感关系扩延至 社会 ,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喜欢斟酌情理情面”的生存特性(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 》,见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8页。)。他这是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情感的寻根,并把这根确定在“家”的血缘情感上。林语堂在 分析 中国文化精神时,对比中国与英国民族文化的异同,也得出结论说:“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 理论 ,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说中国文化,本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并没有难懂之处。”(注: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引自《中国文化概论》,第195页。)林语堂所说的“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这正是中国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以人情为前提”,便是体验的文化特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的当代学者张岱年,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四个要点,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及天人协调。细究他这四个要点,会发现这些要点的形成,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具出于重行为目的、重行为反馈、重行为体验的实践理性,直觉体验及情感体验是其基本理性特色。李泽厚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提出一个“乐感文化”的命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概括为“乐感文化”,以此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他对此概括说:“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识逻辑的清晰。总起来说,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李泽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乐感”型、审美型的概括,正是突出了这一文化的情感体验的本性。我在《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一书中,曾专题分析过这个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的本体特征概括为情感体验特征,并分别对之进行了文化特质的、文化思维的、文化哲学的及艺术论的思考(注:拙着《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2.“情”的本真规定
先考察一下“情”的字义。“情”,《说文》:“人之阴气,有欲者。”按阴阳说,阴阳为生命之本并化生人的万有万能,说“情”为阴气,这是将“情”推到了生化生命的本真之处。段玉裁注,情乃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欲,是生理 自然 需要不学而能,这又是将“情”归入人的本真状态。《吕氏春秋》强调“情”的天生自然:“欲有情,情有节……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吕氏春秋·情欲》)这是在确定“情”的生命自然即直接的感官根据,是耳、目、口对声、色、味的自然欲求。“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然又是这生命活动的本真。《尚书》“情”有一见:“天畏fěi@①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孔安国《尚书传》对这一“情”字作“人情”解,即民群的真实感情,“人情”被看作天是否辅助的尺度。此后,“情”便与事物之真、实相关,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关。“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左传》庄公十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鲁有名而无情”(《左传》哀公八年);“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国语·鲁语上》)。这“情”,都是事物、事情的真实情况。《论语》用“情”两处,都与人的自然本真相关:“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
因为“情”本义于生命本真状况,所以它常与另一个表生命之本真的字“性”连用,称为“性情”。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这“天”便是自然,自然天赋。荀子提出“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情”是自然天赋的本质,是生命的本真。荀子之后,“性”、“情”、“欲”三者关系的哲学之思也就逐渐多起来,形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辩——“性情”之辩。
中国古人热衷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本真追问,把本真作为文化建构、艺术实践的基点或出发点,并在本真追问中把握判断事物及行为的标准。如儒家先哲孔子与孟子,在推衍他们的人世之道与道德之天时,便从本质设定出发。“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羞耻感在这里被推为不言面喻的本真标准;“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情”被指定为“性”本善的根据;“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这是孟子对羞耻感的进一步的本真强调。管子本于“情”的人事道德推衍更为直接,“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管子·禁藏》);“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管子·君臣上》)。道家进行的道德推衍其实也本于“情”,与儒家对“情”的人世社会比附与推入不同的是,道家本于“情”却比附于“自然”,再由“自然”而推入社会人生;当然,道家对于“情”的本真设定或本真理解也不同于儒家,道家更强调“情”的自然性。“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无情不是否定“情”而是不动情,这里有一种超越喜怒哀乐的更为广博深厚的“情”,这便是宇宙人生之自然,是融于宇宙大道的生命冲动。至于墨家的“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墨子·亲士》);法家的“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韩非子·难三》)等,也都可以看出他们按照各自的“情”的本真理解,进行各自的“情”的本真推衍与强调。
二、建构体验世界的心灵方式
在中国古代,本真之“情”涌发本真之欲,本真之欲又实现于本真的血缘亲情关系。血缘亲情关系是“情”的本真关系。由此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便也可以说是充分社会化的血缘亲情关系的意识形态。而建构、接受、运用这样的意识形态,又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这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必然也是血缘亲情关系型的。所谓思维形态的血缘亲情关系型,即它与血缘亲情关系共同发生与发展起来,它以血缘亲情关系为思维对象,在对血缘亲情关系的思维中不断完善这一思维结构,并思维地解决社会化的血缘亲情关系的各种问题。对这一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我在《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一书中,曾将之概括为情感关系思维或情感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①客观的感情依据;②思维主体现实体验向感性对象的融入;③过去经验对于现实感性对象的渗入;④表诸于形象或含有形象因素的一般判断形式(注:拙着《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在这样的思维形态中,“情”有了本真之外又一重原创意蕴,即它是中国古人建构与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经由这样的思维形态,中国古人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有直接的关联——社会文化活动直接关系着艺术活动,艺术活动也直接关联着日常社会文化活动,甚至不少时候,社会文化活动就是艺术活动。
且看《吕氏春秋》这段话: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 音乐 ,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叹,有进乎音者矣。大飨之礼,上玄尊而俎生鱼,大羹不和,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吕氏春秋·适音》)
由音乐而民俗民风,由民俗民风而理义之行、国家之治。对这段文字的解读,不仅要注意它指出了艺术与人伦 政治 的关系,更要注意它对于艺术与人伦政治的情感关系的揭示,它们面对同一的情感关系,把握同一的人伦情感世界,所以它们才能由此及彼地互相指认互相通达。艺术与人伦世界的同一关系,在孔子论诗、庄子寓言、韩柳论文中都被作为通则而运用,这不是他们对于艺术的误解与偏见,而恰恰是他们对艺术与现实生活情感思维同一性的深悟。
对“情”的思维形态意义,中国古人多有论述。如《淮南子》,从“情”感物而生并形于外的方面加以揭示:“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淮南子·缪称训》)汉代从石渠阁奏议到白虎观奏议,涉及“情”的思维规定性,并以此作为制定国家等级制度的根据:“情性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诀》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白虎通德论·情性》)这指出情是阴化、静也、贪也、利欲也;性为阳施、生也、理也、仁也,二者在生存的心灵活动中各有所重,各有其活动特点,又相辅相成地展开心灵活动的过程。东汉王充基于情性阴阳之说,指出要更好地运“性”用“情”,就必须注意对之制约与调节:“故厚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论衡·本性》)这实际上是揭示了礼乐乃“性”、“情”思维的结果,因此礼乐才能反转来制约与调节性情。刘勰基于“情”的过程性理解,进一步作了“情”的艺术思维的揭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这指出“情”组织文学语言,使之由隐而显的表现功能。“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这是揭示“情”的文学发生过程。“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这是在讲“情”与艺术想象的关系。
体验情感型思维形态关注现实与 历史 的各种情感关系,包括人与人的情感关系,人与社会的情感关系,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长于对这类情感关系进行丰富复杂的情感体验,并以真切细腻地表现这类情感体验为思维目的。这一思维的艺术成果便是创造出生动地表现各种情感关系与情感体验的艺术形式。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在进行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古代美学的对比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古希腊美学也并不否认艺术对人的情感的 影响 和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它更为强调的毕竟是艺术对现实的再现的认识作用。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首先是艺术的情感方面,它总是从情感的表现和感染作用去说明艺术的起源和本质。这种不同,也分明地表现在东西方艺术的发展上。”(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由此可见,“情”确实是中国古人情感关系地建构与把握世界(包括艺术世界)的思维形态与心灵方式。
三、创生艺术的母体
强烈的抒情要求形成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的明显差异。突出的抒情特征的形成,则源于中国古代文艺史中抒情艺术的早熟及对于各种文艺形式的创生。
中国古代最早形成自觉并走向成熟的艺术是音乐,音乐的抒情本质早已不言而喻。
固然,不仅中国,在世界艺术史中,音乐也是出现最早的艺术,这已被很多学者认同。不过,最早出现的艺术与最早形成自觉并走向成熟的艺术并不是一回事。
《周礼》有一段话,证明至少在周初,音乐的创作与 应用 便已进入自觉阶段:“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②、大武……”。(《周礼·春官·宗伯》)尽管有资料证明,“礼”的观念周初已开始形成,但“礼”在当时生活中的作用却无法与“乐”相比。“乐”所感受并表现的秩序与和谐进一步理性化,才明确为“礼”。“礼”是规定了的秩序与和谐。对此,中国古人早有认识——“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乐”先于“礼”又通于“礼”,“乐”、“礼”共同规定与生发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乐”、“礼”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情感体验与情感理性形态,滋润与繁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抒情特征。
而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早熟,也证明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情”的根基。
中国古诗“情”的根基与“乐”相通,中国古代文艺史不乏诗乐舞原本一体的记载。如刘勰说:“或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文心雕龙·明诗》),孔颖达说:“大庭有鼓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昔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诗谱序正义》)诗生于歌舞,亦即诗生于“情”。
“乐”与“诗”这类抒情艺术在中国古代率先自觉并成熟,在于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根基——人伦情感的艺术形态,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感召力和普通有效的接受效果,使统治者与施教者把它们用作人伦 教育 的得力手段。中国古代抒情艺术率先发展与自觉,是人伦文化建构的必然。这个过程中,孔子以“乐教”、“诗教”为核心的艺术观同时也是文化观,起了重要的理性指导作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对此作过分析,透视了其中血缘亲情的文化根基(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很有说服力。
总之, 中国 古代文学 艺术 根基于中国古代人伦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伦情感本质就 自然 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由于“乐”、“诗”抒发人伦情感方面很早便自觉与成熟,也由于孔子的理性概括与引导,使的“乐”、“诗”的“情”的本质规定成为后来因“乐”、“诗”而生发的其他门类的文学艺术也获得了“情”的本质规定。
四、文论诸范畴的总领
文论是文学实践的 理论 形态。“情”的文学艺术的原创意义体现在文论中,则在于它具有范畴总领意义。也可以说,“情”的文论诸范畴的总领意义,正证明它的文艺原创性。
“情”的范畴总领意义可以从思维形态、文论范畴发生及范畴构成角度加以论证。
①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都是情感体验思维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成物,分有情感关系的本体属性并运用与 发展 着情感体验型思维。所不同的是,文化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创生与建构,由于 社会 实践的物质规定性,情感体验型思维常因实践对象的客观定性而难以充分施展;即是说,对象的客观性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它否定体验的主观性。这时,活跃的便只能是主体的认知而非主体的情感。在文学中,对象的客观定性消融于文学创作主体,情感体验的特征性思维有了充分实现的条件。充分实现的情感体验思维,创造着情感体验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形成与之相应的文论范畴。由此说,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也是情感体验型思维的产物,是这一思维形态的理性成果。“情”在情感体验型思维中具有发生、运作、课题与衡定意义,“情”的生理与心理规定直接成为思维规定。作为范畴的“情”正以文艺的情感活动为对象,以揭示情感活动 规律 为旨归,因此,“情”范畴的 研究 也是情感体验型思维本身的研究。文论其他范畴孕生于情感体验型思维,所以也正在“情”范畴的研究之中。换句话说,“情”的情感体验型思维研究自然蕴含着文论其他范畴的研究,而且在文论其他范畴的研究中处处见出“情”的规定。
就拿“理”来说,在西方,“理”与“情”是对举的两个范畴,它们经常在二元对立的情况下运用。在中国古代文论,“理”却是“情”的构成范畴,“理”主要是揭示“情”的发生、运作及表现根据。如刘勰所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叶燮所说“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原诗·内篇》)等,都是在讲“情”、“理”相一的关系。李泽厚则把这种“情”、“理”相一相融的关系概括为“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国的智慧”(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11页。)。
②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都是“情”的生发
如前所述,最充分地体现“情”的本体意义的艺术是乐与诗,乐与诗的最先自觉与成熟,决定了它的理性形态“情”范畴是最早提出的艺术论与文论范畴之一。
《国语》记载周王与单穆公、伶州鸠关于声乐与声乐接受效果的对话,虽没有直接就“情”字展开,但二人由声乐大小、强弱、疾缓作用于感官引起的体验与感受的 分析 ,及对这种微妙、复杂的体验与感受所唤起的道德感与所引起的道德行为的分析,都已深刻涉及情感心 理学 内蕴,都能从中看到较丰富的情感唤起与情感运用的经验(《周语下》)。《国语》还有一段“情”与“文”的对话,涉及“情”、“貌”、“言”的关系:“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赢氏。……(宁赢氏)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国语·晋语五》)这段记述提出了“情”与其外部表现相合相离的 问题 ,也涉及“情”的话语表述问题。这类问题对此后的“情形”、“情言”、“情貌”、“情理”等艺术论与文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此后文论众多范畴课题的提出与展开,如“诗言志”课题、“性情”课题、“形神”课题、“神思”课题、“比兴”课题、“象”与“象外之象”课题、“旨味”课题、“虚实”课题、“言意”课题、“意境”课题等,无不与“情”的文学发生意义、“情”的范畴延展意义密切相关。
“情”对于“志”、“礼”、“性”、“心”、“德”、“神”这类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基本范畴的发生意义,更可以由孔子及其后学对于《诗》的多元解释见出。对艺术深有造诣的孔子,对《诗》却经常作非“诗”的解释,这类解释看似出格,其实,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以情感体验思维为特征的,文化系统的众多方面、众多范围都与“情”相通,可以互相生发彼此转化,就会少一些大惊小怪,这类解释只是顺“情”成章。如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致,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治《齐诗》的匡衡总论《风》诗时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这都是在强调艺术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情感同一性,艺术与各种社会活动都是“情”的生发。这一点在《毛诗》序中说得更为清楚也更为具体。如《召南·草虫》序,说这是“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郑风·将仲子》序则说是“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这类读解,不管距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是近是远,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孔子以降,确有很多哲人与文论家悟及“情”在生活中在文学与文论中具有重要的发生意义。
③“情”对文论诸范畴的构成
“情”对文论诸范畴的构成,是指文论诸范畴都合于“情”的定性,都分有“情”的性质。由于文论范畴为数众多,无法逐一分析,这里只能举诸范围之要,择几个基本范畴,进行“情”的构成性阐释。
a.“意”与“情”
“意”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它是文学创作的所欲表达,文学作品的已然表达,文学接受的理应获取。
“意”的提出与运用由来已久。《易传·系辞》中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此说法后来广为引用,它不仅提出了言、意、象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意”不可尽言的属性。《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又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些说法都认为“意”是有一定认知 内容 的心理活动,它要经由语言而表述,但语言又无法对“意”充分地表述。
陆机大概是最先在文论中运用“意”范畴的,他的《文赋》可以说就是为了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问题而作。此后,范晔的“情志所托,以意为主”(《狱中与诸诸甥侄书》);杜牧的“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答庄元书》);邵雍的“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论诗吟》);刘熙载的“意在笔先”(《艺概·文概》)等,都非常强调“意”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但也都认为虽则“意”之于诗文绝对不可或缺,但诗文又难于尽“意”。“意”的无可尽言,是中国古代文论对于“意”范畴的普遍看法。
那么,“意”为何物?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却又言说不尽或言说不清?对这个问题,范晔的一段话说得很精当:“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狱中与诸甥侄书》)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范晔从“意”的心理发生角度体悟到,“意”乃“情”与“志”的统一,是创作主体有感于生活而形成的“情志所托”的体验,这类“情志所托”的体验酿成具体的文学创作之“意”,这“意”便是具体化了的“情”、“志”融合的心理活动。“文”不能尽“意”,在于构成“意”的“情”的活动变化极为微妙,“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狱中与诸甥侄书》)对“意”的“情志所托”的心理发生过程,范晔之前的陆机曾进行形象地描述,揭示了“意”发生的感官依据,在“意”的发生中有“志”的萌动,有“史”的感悟与“文”的陶冶,而这一切又都涌荡“情”的波流,这才“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文赋》)。
正是情感体验的浑然而动和微妙之动,正因为“情”包融着感性、心志、既往的文史修养与现实的情境激发,这一切都难于为语言所分解所确定地指认,这就决定了“情志所托”的“意”的非尽言性——“意”的非尽言性来于“情”的构成。
b.“风骨”与“情”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高标准追求,也是很高层次上被运用的鉴赏与批评标准。
“风骨”的不易求,一个重要原因是“风骨”意蕴的不易把握。这种不易把握与“风骨”追求所必然伴随的“情”的活动分不开。“情”一经融入,大量无可言说的东西便活跃起来,更何况“风骨”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体验,就是一种情感体验效果。与构成抒情作品内容的情感不同,“风骨”的情感体验是对于作品的情感体验内容所进行的表现的体验。
因为“风骨”是对一定内容的表现情况的体验,所以有“风骨”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范畴(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风骨》、寇效信:《论风骨》、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都持“风骨”乃内容与形式的说法。);也有学者注意到“风骨”的情感体验性质,把“风骨”理解为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注: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65页。),并将之纳入道德规范。
宗白华曾深入地研究“风骨”,他的看法被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论者所引证。这里且把宗白华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摘引“我认为‘骨’和词是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它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想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注: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这段话确实指出了“风”从情感中来,“骨”从思想中来这一层意思,但从什么中来并不意味着这来者就是什么。说“他从家中来”,这来者是他而不是家。这是简单的类比。“‘风’从情感中来”,“风”未必就是情感或情感倾向。“骨”也是一样。
那么“风”、“骨”是什么?还是前面那句话,“风”、“骨”是对于情感体验内容所进行的表现的情感体验。所表现的情感体验内容自然含有一定的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自然也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在其中,但宗白华并未止于此,他强调的是如何表现这一定的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他分析刘勰的“结言端直”,说这“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辨”;他说“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毫无疑问,这都不是说表现什么而是说如何表现,是就表现特点与表现效果而言。
从中国古人长于进行的类比思维来说,他们总习惯于把某种言说不清的属性、功能、效果等通过形象比喻加以述说。这种类比思维的要点在于被述说的东西与用来述说的东西,必在比与被比的基本点上能唤起认知与体验的一致性。“风”取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性类比,当是自然流动,无所阻碍。“骨”取于人或动物的机体之骨,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性类比,当是坚实鲜明,刚正硬朗。不管对“风骨”的具体内容做出多少解释,都应该就类比的基本特征展开。刘勰“风骨”论的意蕴正是在如是的特征性中展开的,“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guī@③璋乃骋。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文心雕龙·风骨》)。这些类比的精言妙语,确乎有些扑朔迷离,但根据类比思维的一般规律,抓住基本的类比特征,仔细地思索与体验进去,则不难发现,“风”者确实讲的是情感抒发所达到的自然流动、无所阻碍的表现境界;“骨”者确实讲的是思想阐发所求得的坚定鲜明、刚正硬朗的表述效果。不过,无论情感抒发达到的表现境界也好,思想阐发求得的表述效果也好,都是共见于表现的;而且,对这种表现境界或者效果的追求与接受,又都依凭于情感体验。
既然如此,既然“风骨”是以其表现性而见于情感体验的范畴,“情”对这一范畴的构成性,当毋庸赘言。
④“味”与“情”
“味”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范畴。这一范畴的文论意义存于文学文本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是在这接受关系中读者对文本所形成的读解感受。对这样的读解感受,出于类比思维,中国古人觉得这就像嗅到或尝到的令人陶然的美味,“味”便于读解感受联系起来,成为这类感受的指代,“味”也便逐渐被用做文学与文论的接受范畴。
最早取譬于“味”者,大概是《左传》载晏子论“和与同异”(《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以“味”喻一种特殊的 音乐 接受效果,即“声乐如味”。这种接受效果来于音调与节律的相成与相济,亦即和谐,产生的直接接受效果是平心,进一步的效果便是和德,即协调人伦之序。由这段最早的取譬于“味”的文字,起码能找出“味”的三点规定:“味”生于“声”与“听”的相互作用中;“声”被“听”而得“味”,又并非所有的“声”都能有“味”,有“味”之声必是音调节律相成相济之“声”,这是被接受的艺术一方的规定;“味”的接受效果,是接受主体的平心和德。再进一步分析,合于这三点规定而成“味”,就在于被“味”者能唤起一定的情感体验。为什么把这接受的规定确定于一定的情感体验?可以拿出三点根据:首先,音乐作为特殊的艺术门类,就是情感体验的艺术,它无法表述更多的认知内容,它是通过声音变化唤起情感体验,所以,产生“味”的这种“声”与“听”的相互关系就是一定的情感体验关系;其次,“声”被“听”而得“味”,这能“听”出“味”的“声”其实就是能唤起某种情感体验的“声”,“声”的唤情作用,不同“声”的不同唤情效果,当下心理学已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声音唤起情感的生理根据;再次,“味”的接受效果,即平心和德,也是情感体验的效果,根据情感心理学,和谐音乐的接受,可以平和焦虑、放松紧张,主体可由此进入安适宁静的心境,这正是情感效果。可见,“味”的最初提出,便是意指情感体验的接受过程与接受效果。
此后“味”被引入文学与文论,它的情感体验性质也就一并被引入。文论中经典的“味”论者有三人,即刘勰、钟嵘、司空图。此三人谈“味”都不离开情感体验,也可以说,对他们的“味”论都应作“情”的理解。
如刘勰说:“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文心雕龙·物色》)“入兴贵闲”,“析辞尚简”,讲的就是由“文”而“味”的唤情规定。钟嵘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这里的“兴”、“比”、“赋”不仅被视为作诗的基本手法,这同时也是手法对于相应内容的要求与规定。“兴”与“比”表现“意”与“志”,“意”与“志”都是一定的情感体验,这情感体验生发于“物”,“物”又靠“赋”而入诗,所以诗的“比”、“兴”离不开“赋”。作诗的关键就是协调“兴”、“比”、“赋”三种手法,即所谓“宏斯三义,酌而用之”。这样,“味”的接受效果就可以求得,即使“味之者无极”。可见,钟嵘的“味”同样是情感体验的接受效果。
司空图谈“味”更恍惚一些:“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tíng@④蓄、温雅,皆在其间矣。……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与李生论诗书》)在司空图看来,“味”是一种难于指陈的接受效果,“味”具有超象超知的接受性。超象超知又有所接受,司空图便把“味”更充分地交付给情感体验,因为从心理接受根据而言,惟有情感体验才能超象超知甚至超验地接受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微妙信息。对此,国外的格式塔学派、瓦尔堡学派及现象学心理学派已多有揭示。司空图当然未达到这些当代心理学的专门程度,但司空图凭丰富的艺术经验对此却有所感悟。至于司空图此段文字所提出的单一之“味”与调和之“味”的差异,对调和之“味”作的“醇美”及“味外之旨”的赞美,则是对“味”的情感接受关系及情感体验进行了更细微的区分,提出了更高的情感体验要求。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非下加木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4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8--02
世界园林有东方、西亚、欧洲三大系统,中国古典园林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东方系园林以我国园林为代表。中国古典园林是指以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山水园林形式。中国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极具艺术魅力,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渐受到破坏,生态文化建设随之日益受到关注。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这一角度出发,我国的古典园林艺术对当代具有很大的启示性作用。本文以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理念为基础,结合当下的生态文化建设,探讨古典园林艺术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当下的生态文化功能。
一、何谓“生态文化”
在探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的生态文化功能之前,有必要对“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加以界定: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生态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它更强调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中从多个方面体现了生态文化思想,对当今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园林文化建设具有很好的传承与借鉴功用。
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典园林和现代城市景观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即设计出更加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环境。由此可见,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对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借鉴意义。本文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古典园林进行解读,对古典园林的生态美学意韵进行探究,从中探寻出可供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借鉴的合理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空间布局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园林通常是由实体和空间这两部分组成的。实体是指建筑、山石、植物等造园要素,是产生视觉形象的主体;而空间是指包围实体的空场,是人们休憩游赏所必需的。实体构成空间,空间围绕实体。所谓“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等园林艺术效果,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空间所能展现的,而是需要把若干空间按照一定的序列组织起来,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动态感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空间布局上充分体现了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模仿自然的生态文化特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个造园手法――借景。计成在《园冶》中强调:“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是指在造园时要借助于园外的自然山水景色于园内,这就避免了园内景色与外界的纯自然景色相脱离的弊端。园林作为人工空间的营造艺术,必然关注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和谐统一。造园侧重于因地制宜布置一系列院落,需要在园外的人工环境与园内的“自然山水”之间营造一系列从人工到“自然”的过渡性空间。以文人画家为主体的中国造园家更加注重“自然美”,突出“自然”在园林中的统帅地位,因此努力使建筑的人工性弱化,反映在空间的通透性、材料的自然化和布局的自由化方面,有助于将人工性建筑融于“自然山水”。
(二)诗文题词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特质最为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匾额、楹联、摩崖题刻以及“诗条石”等形式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谈及大观园时便论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声色”。诗文题咏,与某些景象相结合,被组织到景象之中,点出景象的精粹所在,阐明景象的思想、情趣,促使景象升华到精神的高度,从而成为园林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园林都是由官宦之家所营建,他们都具备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往往会把自身的审美情趣体现在园林中的牌匾、楹联上,从这些诗文题词的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与外在的生存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旨趣。这里以皇家园林清漪园为例,清漪园位于北京城西北,圆明园之西,玉泉山之东,是一座山水结合、以水为主的自然山水园。“清漪园的总体立意为:静观万物,俯察庶山;崇朴鉴奢,以素药艳;博余名景,集锦一园;外旷内幽,求寂避喧。”[1]关于清漪园中的匾额楹联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园林景物的,有助于人们对景象的更深一层的领会。如宝云阁石牌坊上的“山色因心远,泉声入目凉”,便是以情景交融而点出意境之所在。二是诠释景象原型的,有助于人们对造景渊源的认识。如十七孔桥侧的“烟景学潇湘细雨轻航暮屿,晴光总明圣软风新柳春堤”。这些诗文题词中无不体现着园林建造者对自然山水的尊重与喜爱。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诗文题词中所体现的生态文化理念给当代社会最为深切的启示就在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保护自然,寻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三)意境营造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意境是中国艺术的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极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即主观的理念、感情,“境”即客观的生活、景物。“意境产生于艺术创作中此两者的结合,即创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理念熔铸于客观生活、景物之中,从而引发鉴赏者之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联想。”[2]中国的古典园林主要是在摹仿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加以人工改造,这种改造不单单只局限于布局安排的外在形式方面,更体现于建造主体将自身的审美情趣移入园中,从而营造特定的意境。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意境营造上所体现的生态文化功能就在于园林意境是以“实境”为基础的,对于“实境”营造而言,无论是天然山水园亦或是人工山水园首先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反映自然的原型,在古人看来就是遵循自然界山水、植物、动物的外在结构关系,使园林在形象上与自然风景有共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天然山水园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园址的自然山水本身就给人以非常直观的自然感受。相反,人工山水园在营造实境时受到更大的制约。若要在相对局促的庭园空间中创造震撼人心的自然山水体验,就必须借鉴山水画的表现手法,从自然山水中提取典型要素,将自然山水的典型片断浓缩于咫尺庭园之中。以拙政园为例,拙政园是以江南水乡为原型,通过提炼和艺术加工来营造园中山水的,全园以植物之景为主,以水石之景取胜,充满浓郁的天然野趣。
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沿着“自然―模仿自然―由人工表现自然或改造自然―回归自然”的轨迹发展的。当然,这个回归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更高境界的追求。而今,园林以其绿色空间的内涵,突现了其生态效益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在日益发展完善的城市设计方面,在城市景观的塑造中,生态美会给人提供直观的环境体验和对生活境界的启迪。在城市建设中,越来越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自然,充分认识并合理地开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乃至将整个地球作为人类生态环境的整体来关注。人类本能的对自然的回归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
通过以上几个特点的描述,可以看出在中国园林设计史上一直都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去考虑植被、景观、道路、亭、廊等的布置和安排。尽量将景致置换为天降之景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植被互融,有的利用天然地形的构造来塑造整个园林的景致,或以天然水体为主体,或以山地为主体。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是曲折变化的,但在这条道路上始终保存着自己的那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思想。造园不仅反映出人们委婉含蓄、丰富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而且寄托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园林以朴实无华的自然特征和内敛含蓄的情感表现,对当代的生态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171-01
图腾艺术是人类早期混沌未开阶段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是最早产生、最具神秘色彩的艺术形式之一。虽然远古图腾符号只是简练和抽象的线条,但是它却深刻的勾勒出了千万年的信仰。时展到今天,古老的图腾艺术依然充满着生命力,存在并影响着当代文化。
一、中国古代图腾符号的起源
中国古代图腾艺术与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亦即远古图腾活动密不可分。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从混沌蒙昧的水平刚刚转向对生命和生存的自觉意识。当时,人们通过对自然现象及规律的简单观察,往往用想象及幼稚的逻辑联想加以解释,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理解自然。原始人在对自然界的依赖、适应过程中艰难地生存,并产生了最初的原始。
原始宗教神灵的观念是最初沟通人类与自然之间生存情感的桥梁,并成为漫长的原始时代的精神依托。这种神灵的生命自然观为后世民族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远古的图腾符号,一方面是原始宗教意识中对自然神灵敬畏和恐惧心理的衍生物,另一方面又是一定社会化生存形态中驱邪、避凶、纳吉等主观意识的产物。如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以及凤鸟的形象等,它们都不是现实的对象,而是幻想的对象、观念的产物和巫术仪式的图腾。这些幻想的对象往往寄托着人们良好的主观愿望。
二、中国古代图腾符号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图腾符号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改变,中国古代图腾形象也在不断地演变着。一些具体形态在不断的演变中演化成为抽象的几何纹样。巫术礼仪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成为纯形式的几何图案,但是它的原始图腾含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依然具有着复杂的观念和想象的意义在内。这些抽象几何纹饰并非仅仅为了彰显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点,这些由具体形象而演化的抽象几何纹在当年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而并非今人看来的似乎只是“美观”、“装饰”的作用。
原始图腾符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演变中。一些思想从远古流传到现代,同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而我们现代的生活又使得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内涵更为丰富。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原始图腾的宗教性神圣功能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些社会性的实用功能,如中华民族以旧历年为最隆重的节日,贴对联、年画、财神、门神等,无不以传统图案表达人们追求吉祥、平安、幸福等美好愿望。因此,我们可以说,原始图腾符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演变,但是并没有消失,在今天,它依然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丰富着我们的当代文化。
三、图腾艺术在当代文化中的延伸
中国古代图腾符号是中华民族艺术和文化的宝贵财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中国古代的图腾艺术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魅力,而是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推崇的。
中国古代的原始图腾艺术在当代文化中的各个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在建筑领域里,中国古代图腾符号的影响清晰可见。大约在东汉时期被誉为“百兽之王”的狮子形象在我国的建筑中得到广泛应用。到了今天,我们依然保留着这种传统的文化,在当代的建筑中,人们依然喜欢在修建宫殿、陵墓、桥梁、福地及房屋建筑时,安放上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再如,中国古代的图腾符号也广泛应用于当代服饰设计中。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都喜欢将自己的宗教文化以图腾符号的方式应用于本民族的服饰图案中,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体现着古老艺术与当代文化的完美结合。如我国国内名牌“渔”,它的服饰中大量采用龙图腾符号中的纹样,龙头夸大,突出龙嘴和唇,两只眼睛在一个平面上,龙神多卷曲,形状飞腾张扬,极富动感,图腾图案的运用充分不仅体现了传统服饰文化风格也彰显了当代文化的灵动。
多元化的社会成就了人们多元化的口味和审美观念,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且喜欢古老的图腾符号,并把它当成一种装饰、一种身份的象征。原始初民对于“图腾符号”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在各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并渗透到艺术、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中国古代图腾符号虽然起源于古代社会,但它在今天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成为当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刻的影响着当代文化。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6
第二,解读与还原性。所谓解读与还原.是指精选出各类艺术理论的代表性文章,通过提纲挈领式的分析评论,揭示其理论内容,指出其地位影响等。这种解读与还原是十分重要的,它将古代艺术理论的原貌还原给读者,使读者对其有真切实在的认识和感受,而不至落人纯理论论述的玄虚之境中=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术语体系,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论述表达方式等都自有特点。古代艺术理论之精微深奥,往往只可心领神会,而难以语言表迖将原文还原给读者,这对于习惯于以现代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的当今读者来说,不失为一种理解古代艺术理论的最好方式。全书共选文20篇.这些文章代表了古代艺术理论的精华。
第三,以当代意识为指导,从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剖析古代艺术理论的生成机制及发展规律C本书在论述时,总是努力将古代艺术理论的原理、范畴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展开分析.同时又时时注意运用当代的理论意识进行探索论证。如对古代艺术感应论的论述,就是从古代哲学'心理学、文字学等文化背景上展开的。同时,作者又将艺术感应论置于现代艺术理论的视野之中,并与西方的刺激反应”说、“心灵表现”论、“格式塔”心理学、发生认识论等进行横向比较,通过分析对比,从而揭示出了艺术感应论的深刻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7
诗书画乐相结合。中国文学草创之初就是诗乐舞一体,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端也是以诗论乐论相通。汉魏六朝之际,诗书画乐在表现和功能等方面相通的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入宋之后,在理学“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之下,人们更是自觉注重诗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以画论诗、以书论诗等现象纷纷出现,至清代,桐成派后学中坚方东树在遍阅诸家诗话的基础上予以总结:“诗书画乐理一”①。可以说,注重各门艺术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特征之一。著者尤为注重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书画乐之间的贯通研究。前文论及《乐记》中的“遗音遗味”说,即是从乐论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以味论诗”的现象。著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两大特征就是画意与乐感”[2]51,并分别从“画意”和“乐感”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视觉审美意象和听觉审美意象的生成和表现,对诗与画,诗与乐之间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研究。著者从视觉、听觉等审美感官来研究古代文论并提出“感官诗学”这一课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精神及古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美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如其在《画意:视觉审美意象生成表现论》一文中,对中国诗歌的画意问题从视觉这个感官角度进行了讨论,提出“直视”、“悬视”、“内视”三个视觉审美范畴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诗学审美意象的营构方式及其过程进行论究。“直视”是“物沿耳目,临景结构”,“悬视”是“登高远眺,笼罩全景”,“内视”是“视境于心,物在灵府”,诗歌创作是诗人借助“直视”,“悬视”或“内视”来观物取象(境)而创作出来的,由此得出“中国古代诗歌的鲜明“画意”性与诗人的视觉审美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9的结论。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追求“远”的创作精神及中国古代诗歌的“画意”性特点的根源。著者认为,“书画艺术创作的不同,与文学创作差相近似,并且又是共同影响、相互贯通、并生激荡的。”[2]136据此,著者常将古代文论置于哲学、宗教、绘画、书等组合成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如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就充分注意到禅宗的南顿北渐之别对中国画论、书论的影响,认为:“以南北宗派来区别画学的南北流别,这种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2]132六朝文论向来是著者治学的重点,与之相关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研究特点,尤其在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著者认为,“从《文心雕龙》创作论方面,我们最能看到其受到六朝时期玄、道、佛思想的深刻作用,也能看到其对书、画、乐等艺术理论观点吸取和包容的特点。”[2]209故对其进行研究,也是本着这一研究理念的。在《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一文中,著者将乐论、画论和文论结合在一起,以《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及陆机的《文赋》为主,对六朝审美心物观演变过程及其对刘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将诗书画乐与儒道玄释融为一体,堪为著者治学理念的典范之作。
史、论、考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的发展面临转型的问题。人们提出诸如语言学转向、主体性转向、文化学转向等诸多观念,体现了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努力姿态。其实,无论怎么转向,都离不开对历史文本正确解读。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应该向文献学转向可能更为合适。中国古代文论虽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总结而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灭物我的审美心态,以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就是诗性话语这一特征。随意性的、体悟式的意象批评到处可见,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思辨严密、概念明确,往往难以确解。因此对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文本进行历史还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论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侧重于“史”,或立足于“论”,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论、考相结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说必考之有据,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论自身的逻辑性,自足性。这使得本书立论尤为平实,公允。如在《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新论》一文中,著者对古典诗学中的“味”、“韵”、“境”等范畴,既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探其流变,又作“论”的剖析,寻其真义,并对“味外之旨”说与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大致说来,著者精于考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证为主的研究,如《司空图家世、信仰及著述问题综考》、《司空表圣诗集辑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论,考论结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证。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中带考,析论之中,凡所征引,务求真解。如《〈乐记〉“遗音遗味”说及其审美观念之发展》一文,先就《乐记》编撰问题进行一番考证,既为论题“遗音遗味”说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又解决了其渊源问题。在探讨《文心雕龙》中的儒学思想时,对其古文学派的立场及其对今文学派的统摄与汲取,既对《文心雕龙》本身之观点进行辨析,又考征他说予以支撑。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证释。注释是对论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其本身就是论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极其注重注释的严谨和规范,并常加按语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诗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后代诗人妙悟自然,寻觅本体意义的山水诗的先声”后,所加注释就引《世说新语》之《文学》第85则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评孙绰、许询诗,以及评价东晋玄言诗之说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并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目加以辨析,认为:“檀道鸾只是说玄言诗风,‘谢混始改’,但开始逐步向山水诗写作过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转而说是玄言诗孕育了山水、田园诗。”[2]95这种注中考的方式,既强化了论证的力度,也强化了研究的深度。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8
一、艺术・考古――学科交叉新思维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专业性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有许多已经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艺术考古概说》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艺术考古学基础理论,对学科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归纳。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出有关艺术类考古学的条目,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学科的正式提出和设立。《艺术考古概说》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基本理论构建,指出,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说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条目,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音乐史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也成为我国明确设立“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的依据。作者依据上述文献,对艺术考古学的分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进行了阐述,说明艺术考古学是探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探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许多艺术遗迹和遗物,凝结着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艺术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并且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补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学、艺术学研究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指出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头・田野――研究领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类介绍中,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推动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关注,两个遗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属首次,它们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两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四川省艺术考古的全面研究、开发、转化、利用,打下基础。例证、图片丰富,每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标准,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证中的扎实案头工作。
我国艺术考古理论的探索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影响,书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中国美学、音乐学、甲骨学、考古学、古建筑学的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作了论述。如我国第一代美学思想家朱光潜、宗白华先生;我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杨荫柳先生;我国第一代考古历史学家李济、郭沫若、夏鼐、冯汉骥先生;我国第一代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童、杨廷宝先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学后,回到中国,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古物考证、文化内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论等方面,填补了中国某项专业理论研究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美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学等理论研究之先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思维,也在这些专科研究过程中产生。
三、实用・前瞻――文化产业强推动
艺术考古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成为艺术事业建设中快速发展的一种艺术类型。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将成为文化艺术事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强势品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丰富国内大众文化鉴赏娱乐活动中,都会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展演、影视市场上不断创新的类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精神文化起源。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艺术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综合研究机构,出土文物的调查研究受到行业管理约束,各类艺术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测量”等专业性强、技术上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综合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专业课程、建立艺术考古研究协会等设想。在书中,作者还从打造精品品牌、推广多媒体制作和传播、规范旅游区开发、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宣传、筹建艺术考古专业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四川地区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建议。在开发转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归结原因是缺乏资源整合与合作开发。四川应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资源和考古人才,推动四川艺术考古发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焕新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9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著、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著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公元1644年)[4](P.2)。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下限受考古学年代范围的制约,也应该在明朝末年。
由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古代,这样,一方面,体现现代科技和艺术成就的电影、电视、摄影艺术以及设计艺术中的工业艺术设计、视觉媒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艺术门类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时间性、时空性和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曲艺、杂技也由于事过境迁,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静态地展示出来,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作为艺术遗迹的中国古代雕塑大多是留存于地面上的古代艺术品,通常是经过考古调查得到的。昔日辉煌的雕塑艺术品因长期暴露在地面上,直接经受着天灾人祸的摧残,渐渐变得残缺不全、伤痕累累,只有那些创作题材上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思想的雕塑艺术品才被妥善保管、得以幸存。艺术考古学的雕塑遗迹一般可以分成宗教性建筑的雕塑遗留和皇室贵族陵墓前的雕刻遗留两大类。中国古代宗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开山凿窟造像的石窟寺艺术方面,此外,寺庙、道观中也普遍有雕塑神像,一般有石雕、木雕、铜铸、彩塑等,以彩塑多见。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影响下,按照儒家“礼”仪规范建立起来的。自西汉时期开始,皇室贵族的陵墓前,均摆放着按一定的规范布局的石雕艺术品。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
首先,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象既有以不同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书法等造型艺术品,又在这些造型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内容里,包含了许多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可信、稀有和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具有功利性。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史前彩陶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这井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而后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应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它们都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P.10)、“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5](P.27)。在陵墓壁画方面,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
第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田野考古的墓葬发掘。这些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更具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数量的多寡、艺术价值的高低、所包含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否,都与各个时代的埋葬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五、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艺术图像学是释读古代艺术品的必由之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的阐释行之有效。宗教艺术品是宗教借用艺术的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物质化的体现,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或在宗教仪式中专用,另一方面又受到要表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制约,这样,就使得宗教艺术品具有程式化的相对一致性的特征,也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规定性,使宗教艺术品与宗教教义和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6](P.4),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而是紧紧围绕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礼制,表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宗教和宇宙观念等内容,对它们的图像学解释的要旨也尽在于此。
中国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以及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古代艺术品的创造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方式和习俗、审美情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外化,是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古代文献都能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尽管这些古代文献资料由于历代的传抄,其间有较多的后人附会误传,可能存在着不少不真实的成分,但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含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礼义制度和埋葬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
六、艺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由田野考古学提供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创造者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而且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中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古代艺术品同时具有政治思想性和宗教色彩。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与这些学科构成了密切的联系。
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在近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文人创作的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方面。与传世的书画艺术品不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很少与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艺术种类多为金属、陶瓷、玉石质地的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纸、帛、绢质地的绘画、书法艺术品因在地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好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必要补充。此外,艺术考古学也为艺术史研究对象提供鉴定方法和断代依据。
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民族学资料又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艺术考古学为探索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等都还未分化出来。原始艺术,无论是歌舞还是岩画、雕塑,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它还是巫术或宗教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一种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一种交流信息的交际活动,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生产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是解释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光直先生正是运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有关道士使用龙、虎、鹿三juē@①与天神沟通的记载,从解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鹿图像入手,阐述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的[7](P.320)。
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民艺学的积极倡导者张道一先生,在阐述民艺学的学科性质时,明确提出了民艺学与艺术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8](P.291~292)。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领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横跨考古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自然而然地与民艺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首先,艺术考古学为民艺学研究民艺发展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对民艺历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于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其次,中国民艺学的理论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有指导意义。民艺学对本元文化和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和层次的划分,对其相互关系之间的研究,为系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方便。有了这样的分类以后,对研究属于不同层次的古代艺术品,就可以有的放矢,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背景资料做参考,从而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最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丰富了民艺学的理论。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分析,从中可以找到民间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
七、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9](P.36)。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4](P.3)。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同样,艺术考古学又作为艺术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诸方面,有关社会政治结构、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巫术神话和道教、佛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详实的记载,同样,这些内容也是古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日渐丰富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著作或艺术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远播四海、传之后世。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秦汉兵马俑、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青瓷、唐墓壁画、宋元瓷器,以及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间虽然具有物质文化方面有关工艺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
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和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艺术的起源,不能局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而更应该溯源至人类的远古时期。艺术考古学恰恰能够为这样的探索活动提供确实无误的资料,昭示史前艺术由萌芽、成形乃至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如对称形和圆形的造物艺术规律,萌芽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虽然当时人类打制的石器很难与古代艺术品联系起来,但它们却已经部分地具备了作为艺术品造型艺术的美的形式,艺术起源的探索不能忘却这些看似粗糙的器物所隐含的美和艺术的因素。同样,艺术考古学研究对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石器时代实用性很强的陶质尖底瓶为例,它原是一件用作汲水的容器。这种器物的造型主要是适应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内有较大数量的出土。然而,当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如对居住地的表面加以夯平,尖底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托座,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怎么方便,于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尖底瓶的实用地位便下降了,相反,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和令人着迷的汲水特点,被礼制所采纳、放大,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象征,依样铸成青铜器,置于座右,被称为“欹器”——宥坐之器。表明人类的造物由最初的强调汲水功用,发展到经过彩绘装饰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工艺品,最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礼制的推动,演变为丧失了实用性的纯粹观赏艺术品,造物艺术的发展史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规律:即实用先于审美,先有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创造,再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最后派生出纯粹鉴赏性的艺术品。这就是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条造物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
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艺术考古学研究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缺陷,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考古发现的古代艺术作品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丰富多样性、物质资料性的特征。它们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对象所缺乏的。同时,艺术考古学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仅仅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引用,主要在绘画和书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上限只是到夏商周三代或者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这一现象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考古学家开始开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新领域,并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追寻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大题目,学术研究中都忌讳“大题小作”;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提供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而考古学的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新资料不断涌现,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艺术考古学又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科的交叉或边缘科学,但目前对艺术的研究,无论从艺术的概念定义、起源动因,还是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诸问题,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仅就艺术考古学理论和艺术考古实践中必然碰到的若干问题,做探索性研究,以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 俞伟超.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A].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简史[A].格林丹尼尔著.安志敏译序.黄其煦译.安志敏校.考古学一百五十年[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3] 石兴邦.简谈田野考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J].考古与文物,1981,(3).
[4]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S].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5] 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6]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7] 张光直.濮阳三juē@①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A].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 张道一.中国民艺学发想[A].美术长短录[C].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109-01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运用特定的材料所进行的造物艺术活动,即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纵观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整个的造物历史进程来看,其发生与发展跟同时代的科技水平是并列前行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造物活动所用的材料、功能、造型、装饰和采用的工艺技术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和进步,这是人类对自然物认识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以及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变化的结果。工艺美术作为艺术质的生产活动,它始终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它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飞跃性发展的特征,体现出古代先民对造物科技水平掌握的提高与应用。
首先,科技进步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促进作用,不仅在具体的工艺美术领域随处可见,而且对于工艺美术理论也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中国古代,科技进步不仅开拓了人们所“知”的世界,而且以技术手段不断创造新的工艺美术形式。一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几乎伴随着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发明:没有冶铜技术,就没有青铜工艺美术;没有纺织技术,就没有服饰工艺美术;没有制陶制瓷技术,就没有陶瓷工艺美术;至于以各种材质命名的雕刻工艺美术,诸如骨雕、木雕、牙雕、石雕、竹雕等等,更是与掌握各种材料的技术技巧的结果。科技的进步,也改变和影响着古代中国工匠艺人们的劳动方式。如陶瓷工艺美术,陶车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纯人力劳作的局面,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机械工具。
在古代中国,技术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成为工艺美术发展的“量尺”,技术的进步会促进工艺美术发展,乃至取得质的飞跃。
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丰富了工艺美术理论。技术的进步不仅促使工艺美术领域在内涵上日益丰富,而且外延也不断扩大。中国古代的技术及其重视经验积累和总结,往往与材料学、物理学、化学、建筑学以及人体工程学的基础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为上述学科提供了科学发展的技术基础,它们也反过来促进工艺美术理论的初创和成熟完善。比如作为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的《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又如成书于明代的《髹饰录》作为我国古代惟一传世的漆器工艺专著,是我国制漆技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再如,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的《园冶》,作为一部系统地论述园林建筑的专著,当然离不开建筑造园科技的长期积累。
其次,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一方面,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了科学技术的价值评判标准。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工艺造物的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针对造物、科技等话题,诸子百家竞相发表言论,表现出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展现出了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社会价值的冷静思考力量。如孔子主张“文质兼备”,以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强调内容与形式并重;道家提出了“虚无观”,对工艺美术造物利用“空间”起到积极作用;而墨家重工艺美术的功利性,重视造物实践。而此时期正是人们对于科技的作用、对于科技的目的等方面价值体系建立的时期,他们所形成的工艺美术价值观对科技的的价值评判标准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特别是与民生农业有关的科技,获得了突出的发展。
另一方面,工艺美术的发展也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有效形式。科学是对隐藏在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背后规律的的概括和总结,因其抽象性,往往难于理解,而工艺美术凭借具体的形象,帮助人们理解,这为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比如,张衡设计的世界上第一台用来测量地震的地动仪,便是一件工艺美术品,它借助工艺美术造型,把抽象的科学原理具体化了:它由精铜铸成,外形如一大酒壶,仪器的外表刻有篆文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体外部周围铸有八条龙。而工艺美术中的书籍装帧,各种科技笺谱的设计,更是对古代科技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科技是工艺美术造型的手段,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形态的丰富化,使工艺美术品的实用功能更加合理化。而工艺美术的发展,也通过工艺匠人的技艺经验积累以及对于技术经验归纳的分析、通过对科学技术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影响、通过科技传播工艺品的设计,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购物车(0)
购物车(0)